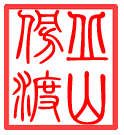迟来的爱
随着人心焕散,纪律松弛,场领导的权力逐渐消失,“不许谈恋爱”的禁令自然解除,处在青春期和躁动不安的男女知青也就如同长久分离的亚当和夏娃,各自开始寻找自己的伴侣。黄普仁结婚了,郭光锴结婚了,刘俊士结婚了,张南岳结婚了,韩一民结婚了……看来是真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了。
黄普仁找的是石枧大队的女知青沈瓜(我们都是这么亲昵地称她),一个胖胖的但很美丽善良的女孩。我与黄普仁是很好的朋友,他会画画,我画主席油画像就是他教会我的,他常带我去石枧玩。
石枧大队在凤凰山下,村子里有祠堂,有庙,有石雕的菩萨,有一座相当古雅的戏台。还有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有布满卵石的阔大河滩,小河上有一座用四根粗大木头搭成的小桥,人从桥上过,牛从桥上过,都倒影在碧绿的水里。
村子前面有两栋红砖平房,便是知青宿舍了。知青们在村里建了一个小水电站,让农民们看见了电灯,知道了机器可以碾米。他们还从长沙城里带来了一批优良品种的蔬菜籽,使村民们吃上了“白”茄子、 “洋”辣椒。如果不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知青们与村民还是相处得较为和谐的。
我去石枧的时候,还有不少知青返城未回。
经黄普仁与沈瓜的撮合,我便结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她个子小小巧巧,是个朴实善良的女孩,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显得有几分腼腆。在石枧大队她很有人缘,大家都把她看作小妹妹。
我清楚地记得我与妻的第一次约会。那晚,我们约会在石枧村前的一条小河边,河边很静,只听见潺潺的水声。我不时张惶四顾,似是唯恐谁窃听到自己那春水充溢的胸房里失去平稳节律的心跳。果然就有了脚步声,而且由远而近,显然是晚归的村民路过。她即刻满脸涨红,慌忙掉头便跑,惶惶如小兽。我追赶不及,心里好生气恼,便迁怒于这些村民,为何偏要这时路过,又偏要从这小河边路过?
自此,我很难和她一道外出。
一次,桃川镇供销社请我去画毛主席油画像。画毛主席站在北戴河,背景是湛蓝的大海与天空,毛主席身着一件深蓝色呢大衣,被风卷起一角,显得伟岸潇洒。画架4米多高,要站在一架梯子上去画。那时,在乡下画这么大幅的油画还是少见的事,有好些人来看。那天,她同她的好友黄友如一同来看我作画,当时,我手上、身上到处是油彩,见她和她的女友来了,慌得我忙去洗手洗脸。后来,她告诉我:“那次我看你画,你知道吗?那脸盆里的水,你刚洗完手,脏兮兮的,可你又去洗脸。当时我就想,大概男孩子都是邋塌鬼,没有女孩照管不行。看来,以后我要来管管你了。”
她这么一说,我哈哈大笑,这事让我得意了好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