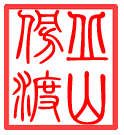路 儿 队 长
我在这个队叫朝阳队,队长叫陈路明,他是1965年从长沙市一中高中毕业下到这里的,这是个极富正义感,极有事业心的青年。他个子不高,却显得虎气生生,经常是一顶草帽,一双草鞋,风里来雨里去,一身皮肤黝黑,看去就像一个栉风沐雨辛劳耕作的农民。
他常常会为农场今后的命运而担忧,老想着要如何把农场建设好,尽管当时大家都忙着抓革命,狠揭狠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每天仍有一二十名知青跟着他上地里劳动。
劳动强度大也较难的活要数烧石灰。先要砍好灰草,要打管备石料,他都是自己带头去干。烧窑自然要请当地的师傅,这不能蛮干,是一项技术活,尤其是如何掌握火候,必须得由师傅手把手地教。女孩子是不能上灰窑的,这是犯禁忌的事。这符不符合科学,没人去探究,反正这是人类的祖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规矩。
火点燃后就要保持火不熄灭,而且要烧得旺旺的,就得不断地把柴草把子往窑内塞,不能有半点懈怠,因此必须轮值。
到夜深了,轮值烧窑的知青就躺在柴草铺垫的窑顶空隙处,让明亮的窑火烤着,天南地北的闲聊。也许是我喜爱文学的缘故,我居然觉得这样的时刻极富诗意。
秋天的夜晚是寂静的,虽然这里那里有几只秋虫在“唧唧”地叫,但那也只能更衬托出夜的寂静。天空像是刷洗过一般,没有一丝云雾,蓝晶晶的,又高又远。繁密的星,如同海水里漾起的小水花,闪闪烁烁的,跳动着细小的光点。四围的山,隐隐约约,像云,又像海上的岛屿,能让人生出许许多多美丽的幻想。
陈路明和我躺在一处,他仰天躺着,双手枕在头下,似在想着什么。
我们都从不叫他名字,而是亲昵地称他“路儿”。我说:“路儿,就我们这几个人能够建设好农场吗?我总有些担心。”
他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现在‘革命’这两个字,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神圣得不可侵犯。”
“我不明白,难道我们现在做的这一切,都不叫做革命了吗?”我问。
“当然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他说,“粮食从哪儿来?天上不落,石头上不生,还得靠人春播夏耘,秋收冬藏。不搞好生产,农场肯定是不会有前途的。”
我叹口气说:“唉!现在这么一个混乱的局面,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有个头啊!”
他说:“我想,大家还是会要搞生产的,农场创办几年了,老是亏本,当然不能再这样亏下去,至少我们自己还得生存。我想待烧完这窑石灰后,便去对土质、水源等进行一番考察,设想出一个较好的建设方案。”
他总是这么乐观,又充满自信。他的这些话,后来写在1968年2月27日他和刘胡子、何清华、韩少和、易宇欣等二三十名知青联名写的一篇《桃川农场向何处去?》的文章里:
桃川农场创办五年多了,农场仍连续亏本,尤其近一年来大量知青返城,使茅草地又恢复到它五年前的荒凉。……革命的知识青年朋友们,桃川农场向何处去?现在是我们决定它命运的时候了!……让我们一起重建农场,重新向茅草地进军吧!
我的回忆之河,常常会闪回那个夜晚,躺在辽阔湛蓝的天空下,感受青春的生命如何在静谧的黑夜中生长、悸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