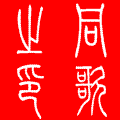我失(she)嘎哒
开春时起,田里的活多起来,忙起来,小组的知青却一个接一个拉开了肚子,如同竞赛一般,最高次数的记录每天都在被刷新。
入夏,几乎人人都拉得脱了形,眼窝凹下去,颧骨凸出来,头晕沉沉,腿软绵绵,终日提不起精神。
可是,一部《买花姑娘》却象一剂吗啡,我们竟然精神抖擞的走了二十多里路,奔她而去,还穿过一条没有人烟的山谷。
一路上,知青组里沉寂了好久的歌声笑语,又在被夕阳染得火红的山路上胡乱冲撞起来。谁也不去想明天还要出工的事了。
这是去看一出催人泪下的悲剧,人们却欢天喜地!其实,大家已无所谓看什么电影,人们渴望的就是电影本身。下乡已有大半年,我们也大半年没看过电影了。
电影一开演,人们便安静了,沉默了。就是在那漫长的嘎嘎乱响的换片间隔里,也只听得到沉重的叹息和嘤嘤抽泣。
…………
回家路上,肚子里的感觉又来了!我有意磨磨蹭蹭,好容易捱到了队伍的最后。我索性停下来。尽管肚子一阵比一阵难受,我还是不想立刻就钻进山路旁的茅草丛中去。
队伍在山谷里无声的蠕动,我怕弄出任何声响,让人回头看见我的狼狈相。
其实这时候谁也不会回头的,人们还在为“卖花姑娘”哀伤,陷得那么深,以至对身边的一切都置若罔闻了。
就是真有人回头,也什么都看不清。山谷里黑森森的,一钩细细的上弦月悬在山头,偶尔从凝重的云块的间隙里挤出一丝微弱的光来。
终于,队伍远了。隐没在漆黑中。我赶紧钻进草丛。
…………
我总算站起来。顿时,脑袋里所有的东西一齐向下跌去,仿佛只剩下一个空壳。脚上则象爬满了无数的小虫。紧接着,一阵不象是痛,却可以击倒任何一条壮汉的痛楚从腿上掠过。
好久,我才站稳。勉强迈出疲软的腿。
深一脚浅一脚的走着,脑袋渐渐恢复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两条腿也伸缩自如了。我却渐渐困惑起来,来时我曾留意过的那几棵狰狞的枯树哪里去了?几口绿幽幽的深潭也不见了!一抬头,那一片被月光穿透的云,也从左边跳到了右边。
啊,我倒吸一口冷气,迷路了!
月亮掉到山后,黑暗填满了山谷。绵亘的山峦象两道巨大、墨黑的屏障,紧紧地夹着我,将我与世界隔开。头顶上只留下一线狭窄的天空,低垂的黑色云团擦过山巅,悄无声息地急驶而过。
看不到一颗星星。我木木的站住。
山谷里死一般的冷寂,什么声音也听不见,连我的呼吸,我的心跳,我的脚步声。但这冷寂中又仿佛注满了不可名状的、震耳欲聋的噪鸣。在山的挤榨中,在云的压迫下,躁动着无数兴高采烈的生命。
我摸索着向前走,终于能在黑暗中辩得出浅一点的黑和更深的黑了。
隐约可见的小路象一条飘忽不定的灰色丝带,我往前走一步,丝带就无声的向前飘出一小截。
突然,丝带断了。我死死盯住前方,那里只有黑洞洞的一片,或许只是半人高的断崖,或许又是不可测的深渊。不管是什么,路毕竟断了。我不敢再走下去。在这本不该有路的地方,为什么还会有被人踩出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