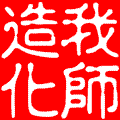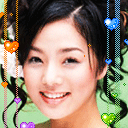劳碌之余,当我躺卧在杂草丛中,百无聊赖地呆望着天空南来北往的云朵,就遥想起远在长沙苦命的母亲。母亲是出生于京城望族的大家闺秀,她的祖父冯汝骙最后一任官职是宣统末年的江西巡抚,《清史稿》中留下了对我这位外高祖的简短记载:“冯汝骙,光绪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后出知川、鲁、直、皖、鄂多省兼任多职。后以理财功升至浙江巡抚。辛亥年移抚江西。武昌变起,赣处下游,举省皆震。南昌军相应和,胁汝骙为都督,号独立,峻拒之。礼送出境,至九江,仰药殉。谥忠愍。”由此可知,我的外高祖遇上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却不会顺应潮流和部下拥戴,当上江西都督、革命元勋,倒便宜了李烈钧那小子。他为表明效忠清廷,竟然仰药自杀以殉。虽然成就了自己的愚忠名节,却没有给后人带来任何好处。
外高祖死后,社会巨变,家道中落,但母亲小时候的生活还是衣食无忧的,她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从事优裕的翻译工作。由于战乱加上婚姻的不幸,母亲辗转来到东北,并跟随我父亲来到了她素昧平生的湖南。父亲解甲归田以后,母亲洗尽铅华,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父亲去中南军政干校学习,家里生活困难,母亲与街坊一起成立织布社,日日夜夜纺纱织布,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她积极参加解放初期的群众扫盲工作,被录用到学校任教,但由于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也就被清洗回家。过苦日子时期,母亲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几件首饰都换成了沾着泥巴的罗卜和红薯,填进了我们姐弟们的肚子,几件压在箱底的衣裳也早改成了我们的童装。母亲经历了太多的离别,五十年代初将我同母异父的姐姐送去荒凉的新疆参军,成了“八千湘女”的一员,六十年代又先后把哥哥冯世续和我送到江永和靖县农村劳动。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以及在文革中遭到无情批斗打击之时,母亲用她柔弱的肩膀艰难地支撑着父亲和岌岌可危的家,她与父亲相濡以沫,相守到老。父亲去世之后,我家的老院子被没收,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被赶到两间狭小的公房居住,并经受着她曾经的扫盲学生、后来的街道干部们的抄家、管制、批斗。
望着天边飞驰的白云,我仿佛听到母亲在向我呼唤:“燕子,你在那里还好吗?”我仿佛看见母亲在那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坐在杂乱的床边,呆望着窗外天边北去的雁阵,口里喃喃地念诵着“又是一年春草绿哦……”。哦,母亲,你是想起了京城故宅门前碧波荡漾的什刹海边微风吹拂的柳枝,还是依稀听见了秋日长空里那听惯的袅袅鸽哨?女儿在靖县的山中为你遥遥祈福啊,这两地相思母女愁情何时能了?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document.write (astro(''));</Script>



[code]<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document.write (astro(''));
</script>



是青春鲜活的生命总要开花结果,但是,苦涩的雨水浇灌苦涩的土地,只能开出苦涩的花朵,结出苦涩的果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心里渐渐萌生出对爱情的朦胧渴望,但对于周围同时下乡的知青同学,我却无动于衷,对当地人投来的异样目光更是充满反感。因为在五中读初中时,有一位同级不同班的男同学与我相互有好感,让我不能忘记。当送我们上山下乡的汽车开出学校的时候,他竟然从送行的人群里冲出来,来到我坐的车窗下,与我握手告别,这在当时算是勇敢了。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说过,但我们的脸上写满着的惆怅,似乎都明白那代表着什么。
近两年的知青生活使我有了切身体会,我要写信告诉还在五中升读高中的他,告诉他在乡下的真实情况,要他千万不要重蹈覆辙,朦胧中也希望得到他的安慰和主意。于是我在信中写道:中学生下乡当农民根本不可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相反,我们今后只会被落后习惯同化。这是文明向落后的倒退,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的流放,是当年苏联将不同政见者流放西北利亚的翻版,等等。信,发出去了,我天天盼望着回信。我相信自己的眼力,我相信自己不会看错,我们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对事物的看法,有过纯朴的感情,我们的心不会因为两年的离别而疏远的。我多么期待着他的安慰成为我打发日子的精神寄托。
在焦急漫长的等待后,回信终于飞来了!我避开最亲密的女伴曹志华,躲进油菜花盛开的田野,用微微颤抖的手撕开了信封,回信却让我大失所望。他在回信中狠狠地批判了我的落后思想,并告诉我,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他和全体同学很快也要奔赴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线了。在信的末尾他写到:惟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人类还有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解放,我们要把整个人生都献给革命都还嫌不够,哪里还有时间来谈什么个人感情呢!
我愤怒地将回信连同信封撕成了碎片,用力地洒到油菜地里,纸片如同一只只白蝴蝶在黄澄澄的油菜花间飞舞,然后不见了。我破碎的心冰冷似铁,如果这算是我的初恋,那它就永远结束了,我已经在心里将它埋葬。我独自强咽下自己酿的苦酒,装出笑脸走回住房,连对最要好的朋友都不再提起。但是我在心里狠狠地说: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再见到他,我一定第一句话就要对他说,恭喜你,革命成功了吧?
一语成真。历尽离乱,三十年后我们果真在长沙一家咖啡厅里重逢了。他回答我问题的答案却真叫我大出意外、匪夷所思。原来他家的遭遇更惨,父亲、舅舅、哥哥先后去世,母亲也被打成“牛鬼蛇神”接受批斗,无家可归的他处处受人监视。在学校传达室拿到我的信,阅后大惊,第一个举动是看值守传达室的校工钟大伯的眼神,揣测他是否拆看过信,再打听是否有人见过这封信,然后就分析我写信的真正动机。因为当时长沙的文化革命正是如火如荼,领袖号召“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路人相遇,互问观点,一言不合,随处就可以成为大批判的舞台、群众专政的阵地。也的确有不少人大义灭亲,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妻子情人、朋友同事之间相互检举揭发,比比皆是。茶余酒后的闲谈、甚至枕边的私房话都抖落出来,成了整人的铁证。也有人戴罪立功,拿话试探,一有响应附和,马上交上去作为替自己减轻罪孽的本钱。我们分开两年,社会复杂,人心隔肚皮,突然来信,安知我不是故意倾吐些反动言论“引蛇出洞”?思想斗争一宿,终于念往日交情,将原信烧毁,连灰都丢进厕所,冲得干干净净,自觉对得起朋友。再义正辞严地回了一信,自信就是拿到中央文革、公安部去,也分析不出个毛病来。不成想假戏真唱,伤透了我的心,也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之路。每忆起这段往事,我心中就涌起对那场摧残人性的政治运动刻骨铭心的愤怒。

</script>[/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