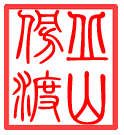霸王岭(三)
赶桃川闹子
一早,队长通知我们,今天领工资。这是我们第一次领工资,一月九块钱,扣去七块的伙食费,每人可以领到两块钱。虽说钱不多,但大家仍很高兴,终究是自己的劳动所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按劳计酬,男女同工同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男女同工同酬我们是实现了,可我们劳动的价值,就只有九块钱么?当时谁也没有去探究,我们狂热的崇拜革命,渴望无私奉献,奉行“斗私批修”,决不做金钱的奴隶,那时,我们充满着无比的壮烈和迫不及待的殉道者精神。
正逢桃川镇赶闹子,队长给我们放了一天假。
桃川镇离霸王岭大约两三里远近,从霸王岭下坡,便能远远望见小镇接堞的屋瓦。镇子不算大,就东西一条大街,街面却很仄,两边全是铺面,平日显得破烂衰败;逢赶闹子,四围各村的人,肩挑负贩着争相赶来,街面便熙熙攘攘,显出一种山乡小镇特有的生机。
我们在小街上走着,这里看看,那里瞧瞧,还不时能碰到从高泽源林场以及其他地方来的知青,往往招呼一声,凑一块去闲聊,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店铺的门面都已大开,饭馆的小伙计在忙着劈柴、挑水;摊贩们已支起篷子,摆出各种货物,有的已摇起皮鼓和铜铛郎,高声招徕顾主;从山里面赶来的瑶家妇女们,把那些大篮子放在自己的脚边后,就从篮子里取出几只鸡搁在地上,这些鸡的脚都是缚住的,眼睛显得慌慌张张,冠子全是红得异样。房檐底下人声鼎沸,裹白帕子、蓝帕子的脑袋四处攒动着。
我们的兴致都是那么高,碰见卖什么的都想挤到跟前看一看,买与不买,总得开开眼。我最主要的是想看看有没有肉买,好些日子没有尝过肉了,心里特剜,肚子特饿。闹子上果真就有猪肉,有几条砍凳上都摆有肉,这在当时长沙城里是稀有的事。我不由自主地在一条砍凳前停下,卖肉的是一个黑黧黧的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见我驻足观看便问:“同志,要不要砍点肉?”他把“同志”念成“洞嘎”,声音古古怪怪的。
我身上只有这二块钱,能买得多少肉呢?我不敢说多少,便小声地试探着问:“买一块钱行啵?”
中年汉子竟然给我砍了一斤三两肉,怎么这么便宜?我眼睛一下睁圆了,忙喜滋滋的提上肉。走不多远,又花五毛钱,在一个瑶族妇女那里买了七个鸡蛋。剩下的五毛钱不敢再花了,得留着发信、买牙膏用。
回队后,我便叫食堂里替我把肉和蛋全炒了,还端了两钵饭(三两一钵),我风卷残云似的狼吞虎咽,巴不得一口全吞了下去。
吃完饭,我忽然哈地一声长叹。这一声长叹,也许包含着人世间无数的欢乐与辛酸。
一种历史的记载
这的确是一种崭新的生活,尽管我们每天都很紧张,很劳累。人,是很容易看重品格,维系自尊,崇尚正直、倔强、坦荡的。我们从城市不远千里来到这偏远的山区,也就是选择了革命,选择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大有作为”,无疑是一个充满信心和希望的热切期待。因此,我每天都感到很亢奋,很充实。也许是我平日喜爱文学,受文学作品的熏陶,便特好幻想,在幻想的空中搭上台阁,一堆又一堆地拼成,一块又一块地砌高。在这些日子里,我情不自禁的在一个笔记本里写了一首又一首的诗:
石工歌
挥锤的手,
砸得石头开;
登山的腿,
踩得石山矮。
头顶祖国蓝天,
脚踏万里石崖;
咱石工,
革命豪情似海!
多少坝,要咱垒!
多少路,等咱开!……
锤把子紧紧手中攥,
铁臂膀上热汗甩。
一锤,砸进三尺地,
两锤,顽石砸成块;
社会主义新图案,
咱一锤一锤砸出来!
赶车
“驾——”
鞭儿催的马飞快:
踏踏踏!
踏踏踏!
车轮滚滚尘土飞,
歌声沿路撒。
赶车的小伙车前站,
像一株白杨,
如一尊铁塔。
摸摸晒黑的圆脸蛋。
看看臂上的肉疙瘩,
喷出一串响哈哈。
谁说赶车没出息,
化肥农具满车装,
驮来个山区美如画!
为建设,
永远不停这双手:
“驾——”
车翻山,
马过河,
一脸风沙映彩霞……
我不想过多地渲染自已的创作,而且很快这些都会成为历史,把它们保存下来,只是做为一种历史的记载。
生活是一幅图画
在我眼里,桃川是很美丽的,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滋润着我的灵魂。1963年12月10日,我在《长沙晚报》写了一篇题名为《桃川风光》的散文:
要过桃川洞,
好鸟飞不动。
这两句话是形容桃川的宽阔和肥沃的。这里山溪纵横,奔泻着叮铃铃的清泉;秋天,成熟的稻谷紧挨着绿色的山岭,就像那玉盘上滚动着的一颗颗珍珠。谁到了这里,谁的心里都要荡起一种对山乡的挚爱之情。
桃川,从前洒满穷人的泪水和鲜血!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杀人如麻,人们只能蹲在山沟,不敢出来。那时,虽有这富饶的土地,又有谁来开垦?
解放后,桃川才熠熠发光了,它吸引着来自长沙、衡阳、冷水滩……各地的人们。我们三百来个男女知识青年,正依着党制定的蓝图,在这里用自己的双手创建人间乐园。
早上,阳光把一脉峰峦沉浸在金黄色的光芒里,林头上笼罩着彩色缤纷的霞光。草叶上还滚动着颗颗明珠,我们就出工了。刈青的姑娘,带着镰刀的磕碰声去了;学犁的小伙子,吆着牛跟着老职工走上了田间小道;锄薯的人们,扛着银锄爬上了绿色山径……山上山下,歌声响起来了:
我们是年轻人,
我们刚刚走进生活,
就有做主人的模样……
你也许没想到吧,我们几个月前都还是长沙市的中学生。我们是抱着建设湘南山区的决心来的,是抱着当一名邢燕子式的知识青年的美好愿望来的。到了农场后,一瞧,这里还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国营农场:农场是去年才开始创办的,两万多亩荒地,还只开垦出一角,宿舍是临时盖的,还没有汽车和拖拉机……这一切一切,怎能不激起我们年轻人的一些感想呢?正因为这样,我们在日记本上写着:我们是来开发山区的,不是来享福的,对革命的热情,不能像水皮上的油花浮头一撩,就剩凉水一缸了。我们坚决听党的话,要干,要革命!……
看,在那绿色的山岭上,我们几行人,几行锄,云里来,雾里去,仿佛在编织着半山云锦。老职工告诉我们,他们去年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野。究竟农场有多大,不知道,只知道这一大片全是农场的范围。满山荆棘、满山茅草……没有房舍,六十四个人就挤在一间破庙里。他们以革命精神,在这千年酣睡的山野挖下了第一锄,播下了第一批种子,也就第一次长上了庄稼:水稻、红薯、芝麻、花生、木薯、槟榔芋……今年,我们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到这里,就更加热闹了。我们付出一份劳动,都有了一份宝贵的收获。
入夜,站在远处看,宿舍排排窗口,闪烁着灯光,多么像是这深山闪烁的明珠!宿舍里有时管弦齐奏,歌声嘹亮;有时则静得就像一泓碧水,因为新老职工们正在埋头学习,有的在看着向李定国同志学习的文件,有的在认真阅读《毛泽东选集》……
战斗的生活,这还是起点,更紧张的战斗,还在前头。桃川,这个暂时还不显目的名字,将会放出耀眼的光彩!
在我看来,生活就好比是一幅图画,只有自己去亲手描绘,渗进自己的心血、汗水,才能形成一幅有意义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