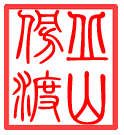偷吃禁果
韩少功在小说《希望茅草地》中记叙了这么一件事:农场每逢放映电影,场里便要组织一批民兵在周围巡逻,发现有谈情说爱的知青男女,便一索子捆上游乡。这写的便是我们农场里的事。那会,我们知青是绝对不许谈情说爱的。我们是来干革命,肩负着世界革命的重任,当然不能搞资产阶级的东西。尽管我们每天男女一块劳作,但彼此都活得小心谨慎。
偏偏有人胆大包天,居然敢偷吃禁果。他叫刘志刚(化名),一个俊俊俏俏的后生,他竟然和一个叫丽丽(化名)的女生好上了,每晚都要出去,至很晚才回寝室。这叫我们全寝室的人替他担了不少的心。每晚回来他都显得极开心,一个人轻轻地吹着口哨,要不就兴奋得在屋里来回走动,要好半天才能上床入睡。我们问过他:“志刚,你啃(吻)过她吗?”“嘿嘿!嘿嘿!”他只是笑,笑得傻乎乎的。问急了,他便说:“蠢话,等你们以后搂着女人时就会晓得该不该啃了。”我们这些男生谁都觉得这事既新奇,又神秘兮兮;既胆怯,又都跃跃欲试。想想自己以后也会搂着个女人,心里便止不住一阵砰砰地猛跳。
一日,队长气急败坏地跑了回来,连连吐着口水。他说他今日去了一处岩洞查探水源,走进洞里黑古隆冬,却瞧见有两团东西在滚动,他以为有什么古怪,定眼一瞅,竟然是刘志刚搂着丽丽。
不知为什么,他们俩个居然没有挨批判,居然没有游乡,大概是队长没有去告发他吧。队长他不怕被斥为纵容资产阶级吗?其实,人类历史同人的认识一样,永远不能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知青生活远不具备产生性放纵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但是在一个灵魂扭曲和暴虐专制的时代,你能无视社会的强大存在,而仅仅苛求个人道德不够完善么?也就是说,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决定人性”(邓贤《中国知青梦》)。
他们俩人居然还有更大的举措,竟然跑出农场,去镇政府扯了“登记”,当晚就举行了婚礼。婚礼极简单,他们买了一点白糖,就用白糖开水招待来客。除了场领导未来以外,我们知青几乎全来了,屋里坐不下便坐到走廊上。我怎么也没有料到,居然会来这么多人,那一双双眼睛里,显然燃烧着渴望和激情。我忽然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人之常情;饮食男女,大欲存焉,是千古之理。有男人女人,必会生性,必会生爱,是能强行压制的么?谁又能区分哪是资产阶级哪是无产阶级呢?人为地强迫自己熄灭任何人的欲念,这个强迫的过程,显然是充满着灵魂的残酷。
那晚上,是我们来农村后过得最热闹、最温馨、最感人的一晚。不知是谁哼起了一支俄罗斯民歌《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大家便都跟着唱:
小河静静流,
微微泛波浪,
树叶儿也不沙沙响……
居然特“资”,但大家极沉醉。唱藏在心里的那个五彩的梦,那个属于各自的秘密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