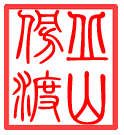冬天里的小屋
我们这里虽属湘南,气温是比长沙要暖和些,但到了冬天仍然是很冷。尤其是茅草地,四围的山不高,很宽阔的平地,树木早已脱落了叶子,所以一眼便能看出老远。西北风呜呜地刮着,旋转啸叫,枯草落叶满天飞扬,混沌一片,简直分辨不出何处是天,何处是地了。
这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们几个人又蜷缩在场部那间小会议室里,在编一期《第一线》。中间一个小火盆烧着炭火,不知刘胡子是从哪里搞来了一点木炭。
刘胡子、陶世普、韩一民、郭光锴、韩少和我们几个人在编着稿件。刘胡子是很认真的,有着极强的敬业精神,每一篇文章他都要认真看,然后提出意见再叫我们修改。易宇欣在埋头刻写钢板,只听到一阵“嘎嘎”的铁笔划动钢板的声响。
我们常常要开通宵班,因为第二天我们都要参加劳动,必须在夜里把报纸赶着印出来。我看过反映当年地下工作者的电影,也是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大家忙着编印报纸,那种敬业精神,常让我十分感动。我忽然觉得眼前一切,与当年那一幕场景很有些相似,只是我们没有敌人的威胁,不用考虑安全问题。想到这里,我往往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有几分自得的样子。
刘胡子便会问我:“你笑什么?”
我说:“没什么,我只是笑笑而已。”
他也就不再问,继续埋头看他的稿子。一副椭圆形的眼镜架在鼻梁上,但是他却把它戴得很低,好像是从镜子上面看似的。
这是没有半点报酬的劳动,但大家都乐意干,用今天的话说,这就叫作“奉献精神”吧。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他们不会理解,或许我们是“大傻冒”吧。
到下半晚了,倦意就渐而袭了上来,难免就想打瞌睡。
刘胡子就会拿出咖啡来煮着吃,并放上点糖。我从未喝过这种东西,黑黑的,怪怪的。刘胡子说:“喝吧,这东西喝了能提神,就不会瞌睡了。”
每人一小缸,苦甜苦甜的味道,很好喝。
喝的时候,刘胡子就给我们讲笑话,瞌睡自然也就全没有了。
在这间小屋子里,我忽然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大家能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做的这一切,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我们却都觉得特别有意义。我常常会在这样的夜晚,在这样一种场境写出一首诗来,我突然清醒自己的生命中还存有一种潜能,那就是我对文字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它使我平静下来,并真切地看到了我自己,知道了自己应该干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