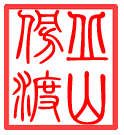收获花生的季节
队上到底具体种了多少亩花生,我至今都不清楚,只知道那么一大片,一眼望不到头,怕有好几十亩或许百几十亩吧。收获花生的季节,那是既忙碌又兴奋的季节,遍山遍野一片旺绿,松软的泥土上发出一股令人酥痒痒的气息。
我们种的全是小籽花生,又叫扯籽花生,收获花生时不必用锄挖,只需手抓住藤蔓往上扯就是,故叫扯籽花生。这种花生虽不及大籽花生好吃,但油路好,出油率高。
秋天的太阳底下,我们男女知青全蹲在坡地上一个劲地扯。太阳很热,熊熊地燎烧着大地。汗从每一个人的头上流下来,豆大一颗的掉在地上。尤其是女孩子们,一个个勾着头,散乱的头发垂挂在前额上,便遮住了大半个面庞,每一根头发都让汗水浸得透湿。
虽然忙碌,但大家心里高兴,每个人都似乎觉得快乐浸入了全身,一下子达到了每个毛孔一般。
我们抓住藤蔓往上扯,自然能扯出好些花生,但仍有不少花生被扯断根须留在了地里,故而我们一上地里,四周就有好些村民提着小锄拎着竹篮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在前面扯,他们便用小锄在后面仔仔细细地刨,居然就刨出了好些花生。我忍不住对队长说:“队长,你看他们在挖我们的花生。”
队长说:“让他们挖吧,反正我们也顾不过来,沤在地里也浪费了。”
这也是实情。我们队才30来个人,天天都忙不过来,哪还有时间把坡地刨得那么干净,这就只能任由那些村民在我们后面刨了。
扯下来的花生,连苗带籽我们全堆放在宿舍阶沿上,码着像一堵堵墙似的。每天早晚,我们就每人搬了张小板凳坐到那堵墙前面把花生从藤上摘下来,一边摘,一边吃,不用花钱,而且尽管吃。我和蒋鼎关系最好,他待人谦和,举止谈吐都显得温文有礼,一张孩子气的脸,掩不住的笑靥使他总显得喜孜孜的,这些都表露出他有一种善良、正直,还有些幽默的性格。每次摘花生我俩便总是坐在一起。
这天早上,我俩又坐在一起摘花生。
我说:“花生能随便吃,这在城里可享受不到啊。”
他说:“这也是的。生花生吃着好,能润肺。”
我说:“我最喜欢吃花生,小时候,每逢过年去给人家拜年,人家给我们的点心里如果有花生,那便会如获至宝似的用衣袋兜着高兴得心花怒放。”
他说:“你知道花生还有一些什么好处吗?”
我说:“榨油呗!”
他说:“我读过许地山一篇写花生的文章,文章中说:‘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生羡慕之心。它只把果实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
我说:“这文章我读过,是写的他和父母一块吃花生,父亲说:‘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他便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父亲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蒋鼎忙朝我嘘了一声说:“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
我知道自己刚才又说了一句犯禁的话,我们现在全中国的人不是都在崇拜伟人么?我父亲其实是个胆量很小的人,就是平日说话不小心,而被打成右派的。想到这里,心里便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忙四顾张望,见大家都在忙活,没有人注意我们的说话,这才把涌到喉咙眼儿的一颗心又放回胸膛去了。
秋日的早晨终究是比白天凉爽,吵人的蝉声早已被秋风吹散,可我心里的那份不安却长久地不肯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