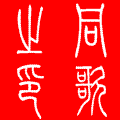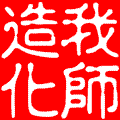转帖“燕归来”的【我的知青生涯】

我 的 知 青 生 涯
1965年的秋天是一个阴云密布、山雨欲来的秋天,我的人生从这个秋天开始,走上了一条凄风苦雨、布满荆棘的崎岖小路。
那年,我从长沙市五中(现名雅礼中学)初中毕业,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家等待高中的录取通知书。虽然自负成绩在班上和年级总是名列前茅,但因为贯彻阶级路线,能否被录取就难说了。当时,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教政治课的
初中毕业的女生,正是豆蔻年华的花季,谁没有对未来的憧憬?谁不是想象着自己将成为
我的父亲出身于临澧县一个耕读农家,1924年,怀着精忠报国的一腔热血投笔从戎,到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参加东征北伐,浴血沙场,九死一生,二十四岁时以战功升为团长。在攻打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伤愈后保送日本军校深造。抗日战争打响后,父亲克服重重阻力,回国报效,担任过黄埔军校第十三期总队长,南京失陷前夕,带队徒步数千里入川。后在陕甘训练民众,组建新一师,亲任师长,开赴抗日前线。抗战胜利后,因父亲打内战不积极,加上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李宗仁等派系斗争,父亲被解除兵权、逮捕问罪,身陷囹圄。出狱后,投奔同班好友陈明仁,任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高参。解放前夕回到长沙,为避免百姓遭殃、生灵涂炭,发起组织在湘军官自救会,与程潜、陈明仁等一道,组织了湖南长沙和平起义。解放后继续在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任高参,在中南军政干校学习结业后,被发表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父亲性情梗直,口无遮拦,在反右斗争中打成右派,主要罪状有二:其一,批评农村大跃进平整土地不应该把老百姓的祖坟都平掉;其二,说在东北时亲眼见到苏军大肆抢掠物资回国。反对“三面红旗”加上“反苏”这两条大罪,让右派这顶帽子沉沉的压在父亲头上,到死再也没有摘下来。降级降薪,时时反省,接受批判斗争。前年为配合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统战部邀我写篇回忆父亲、纪念抗战的文章,我持介绍信去省参事室查阅父亲的档案,被拒。后来黄埔同学会派人去调阅,电话告诉我,已经没有什么有用的史料了,只剩下厚厚的几袋,全部是我父亲的检讨认罪书和思想汇报。1978年接到给我父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以后,我独自一人跑到父亲长满荒草的坟头上,放声痛哭了一场,为了父亲,也为了我自己。
父亲当时已经很衰弱了,戎马一生,他膝下只有我一个女儿,从小珍爱,但在单位反复动员和指令之下,他告诉我,已经在参事室替我报名下乡了。横竖是下乡,还不如主动到学校报名与熟悉的同学一起下吧,何必再给深受打击的父亲增添麻烦呢。就这样,我们五中82名高初中毕业学生在锣鼓声中被送出了校门,远离了家乡和亲人。离家那天,父亲撑着拐杖,努力挺直不再挺拔的腰身,把我送出院门,遥遥挥手告别。走出好远,我忍不住回头,还看见父亲苍老瘦削的身躯倚靠在门边。尚不懂事的我也万万没有想到,父女这一分手,竟就是生离死别的永诀!我下乡后不久,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拖着重病的身体接受批斗,秋天,他就郁郁而终了,其时我在靖县接受再教育,又没有路费,不能回来奔丧。我尊敬的父亲,我坚强的父亲,他没有倒在炮火硝烟、枪林弹雨的战场,也没有倒在重庆暗无天日的沉沉黑牢,却在六十四岁时倒在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倒在了群众专政的震天口号声中!
我和我的亲属们最不能接受的是,去年,为了办理老知青参加社会保险的手续,我从靖县档案馆复印了我这一生唯一的一份档案资料——知青登记表,在这张登记表上,我的“家庭出身”一栏被填的是“伪军官”。我的父亲的经历是复杂的,但不管在旧社会还是新社会,他都是被国家政府堂堂正正委任的军官,如果说不承认他起义有功,不承认他在解放后的军职,称他是“旧军人”也就罢了,但他从来没有加入过汪精卫的伪政权,更没有替日本侵略者卖命,相反他是与日伪军血战到底的勇士,他更是有功之臣,怎么直到现在还要把“伪军官”这样一个屈辱的称号强加在他身上呢?!
来到靖县,我们82位同学一部分下到离县城不远的接官亭园艺场,一部分下放到了飞山脚下的飞山公社塘湖大队,我很幸运地分到了园艺场。所以说幸运,是因为园艺场是出集体工、吃食堂,每月还有几块钱工资,比插队落户要好。我也总结在学校时的教训,一改活跃好强的性格,少说话,多干活,尽量不突出。可是过没多久,“好事”还是落到了我的头上。根据上面的调整,我和曹志华加上两位男同学被对调到了塘湖大队的湾里生产队,我从此才真正感受到农村的滋味。自己种菜才有菜吃,自己砍柴才有柴烧,没有水了,自己去挑,没有厕所,方便时要人放哨。麻麻亮出早工,麻麻黑才收工,一天下来,感觉骨头都要散架了。尤其是挑牛粪下田,靖县用的是用竹子固定的箢箕系,特别高,我个子矮,掂起脚来,箢箕也离不了地,只能勉强拖着走,下到水田里,拖泥带水就更重了。社员又笑话又同情我,安慰我:“你挑担子吃亏,插秧就不吃亏了”。真到了插秧季节,我和曹志华不知深浅,自告奋勇包了一丘大田。半夜两点就起床打着手电扯秧,从早插到晚不敢歇气。扯好的秧不能过夜,直插到月亮当头才完工,腰像要断一样直不起来,勉强爬回家里。
对于我们女知青来说,劳动的艰辛还只是一种磨难,而目睹农村妇女的困苦更使我们不寒而栗。那个时候,当地的妇女是从来不买草纸的,更不用说现在这么名目繁多的女性保护用品了。当时连县城都买不到草纸,我们都是写信要家里寄来,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可以买搓纸楣子的皮纸代替。我很奇怪:当地妇女来了月经怎么办?我偷偷观察她们,发现她们用旧布缝成一个长形口袋,里面装上干柴火灰。我大吃一惊,难怪当地妇女妇科病多,生育率低。在农村,妇女比男人辛苦得多,同样出工,回家后,全部家务由妇女包揽,稍不如意,招来男人一顿打骂,还不能外出诉说。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个女社员在家里被打得哀哀啼哭,想上门劝架,也被旁人拉住:“我们这里夫妻吵架,不兴劝架”。第二天出工,我们撩起她的衣襟,只见她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看得我们心惊肉跳。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如果要我这样过一辈子,那还不如死”。
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子女生育得越多,妇女就越辛苦,但是如果没有生育,妇女就简直失去了生存的平等权利,我们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王大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王大姐个头不高,精瘦能干,下田使牛,上山砍树,样样农活不弱似男子汉。又待人真诚热情,队上安排她来带我们女知青出工,照顾我们的生活。她挑选我担任队上的记工员,每天晚上,我都要到她家里去,在昏暗的油灯下,按照她的口述,将全队每一个女社员的工分记在工分簿上。有时夜太深了,王大姐会煮点东西端给我吃,在那远离家乡亲人、饥肠辘辘的夜晚,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真是不仅充实了我的胃,同时也温暖着我的心啊!
时间一长,我发现王大姐是一人独居,这在当地农村是极为少见的,又不敢问。还是别的女社员悄悄告诉我:王大姐本是从小送到本村陆家的童养媳,因为没有生育,不能为夫家传宗接代。农民虽然都没有多少文化,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却是都懂的,王大姐理所当然地被休了妻,赶出来独居生活,也再没有人动过娶她的念头,到我们下乡的时候已经过去十多个年头了。我们看着她白天生龙活虎、有说有笑,夜里却独对孤灯、自言自语,心里不禁为她悲叹,联想到自己的人生,心也在为之颤抖。我们要是响应号召,扎根农村一辈子,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究竟是嫁为农妇,生儿育女,含辛茹苦一生,还是像王大姐这样独身生活,永远埋葬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呢?那个时候,我眼前只有一片茫然,找不到答案,因为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十年后的1995年,我们五中四个同时下放到靖县飞山塘湖湾里生产队的知青重返靖县,得知王大姐终于再嫁到了艮山口,但是命运仍然没有眷顾这位好心人。她本来以为晚年有靠,且第二个丈夫有个儿子,自己将他视同己出,贴心照顾,总可以人心换人心,继子会为她养老送终。不料想她的第二位丈夫又不幸病逝,已成年成家的继子却不再认她,不仅不承担赡养义务,且形同陌路,不相往来。无奈又加上她依然是一副热心热肠,她又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孩,相依为命一起生活。我们特意赶到艮山口去看望了她,看到她狭小的木板房里,家徒四壁,一无所有,王大姐已然衰老,而怀中的女孩尚嗷嗷待哺,我们都落泪了。俞氏、程树人、曹志华和我都不知道如何安慰她,语言是这样的苍白无力,只能尽力给了她一些经济帮助。
前年(2005年)夏末秋初,我们又再次前往看望,白发苍苍的王大姐正顶着烈日在田野里拣拾稻穗,她除了拣点别人洒落不要的稻穗和山坡树丛中遗落的茶籽,来解决口粮和食油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来源,她穿的仍然是十年前我们送给她的衣服。我们找到当年队上的青年、如今已担任镇领导的熟人,提出希望为她解决困难,镇领导也很同情重视,但后来电话告知我们,当地反复研究后认为她有法律意义上的儿子,不符合五保户的条件,儿子不赡养她,只能帮助教育或提起民事诉讼,但王大姐又不愿意这样做,镇里也无可奈何。女孩已经长大,在艮山口中学念书,这更增加了她的负担。我们再次默然,在她的住房前留下了这张合影。大约是心情的缘故,大好的晴天、返乡重逢的喜悦,没有给每一个人增添一丝笑意,我们的心都是沉甸甸的。
其后,我又多次送去钱物及汇款给她,但是再没有过回音,也不知近来可好。我只能遥望西南,默默祝愿王大姐,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虽然我也知道,我们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虽然我也懂得,我的良好祝愿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是那般的软弱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