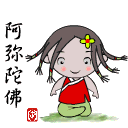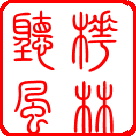到现在都不蛮怕鬼,可能和当年下乡的经历有关吧。下乡年余,我还只19岁,就在邻队和本队帮忙搞过2次丧事,练了胆。从那以后,就喜欢参与一些白喜事,一般人不敢或者是忌讳的路子,单位的同事就喊我。几十年下来,虽然不是搞工会的,也就落得个热心肠的名气。
初当八仙
自从我们七个知青入住苦椎窝以后,本队和邻队冯家塘的青年哥哥们常常三五成群地会来苦椎窝玩。一来二去的,我跟他们也混熟了。
其中一个叫张祖武的年轻木匠也会和他们一起来走走,不过他已经有老婆了。不久,他那新婚的妻死于肝炎。我自然会去帮忙。仗着个大力不亏,我主动提出:抬棺材算我一个!就这样,我领到了一条白毛巾和一双草鞋。社员告诉我,棺材是八个抬的,你就是八仙了。哦,原来是这样啊。
第2天一早,在鞭炮,号乐,土铳和吆喝声中,棺材起肩了。我自我感觉还好,随着大家脚步的移动,灵柩上到了老屋后的山坡上。由于没有路,我们只能在荆棘中艰难地移动。我开始气喘吁吁了。棺材重量,有时候会随地势的倾斜,落在地处低势人的肩上。有几次瞬间如负千斤的感觉,我都是奋力挺住,深怕闪了腰,尽量地凸现高个的优势。
好在傍边社员前呼后拥,有人可以帮衬。也就是20来分钟吧,就到了墓穴。剩下的事也用不着我了,社员们里手得多。他们嘻嘻哈哈地落棺陪土,我坐在一边歇气。心里想,只要不闪腰,没有什么可怕的啊。
我给地主带帽子
我所在的队上有个地主分子,叫张信秋。可能就是40出头吧?他有一个婆娘和一个过继来的崽。崽小得很,好象只有8-9岁。从我初次看到他,一直到他去世,我没有见他笑过。
他那总是哭丧着的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肉,面色蜡黄。眼睛可能是迎风流泪的那种,眼角有泪痕。身体单薄,双手枯槁。社员都讲他有病。确实是一副病容。
他也常常出工,做一些不算太重的农活。我从来没有看见哪个社员呵斥过他。除了队长给他派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和他讲话。队上也没有开过他的批斗会。大队斗过他几次,那是“跟风”。
我有时候想:他一直是这样吗?他解放前没有威风过吗?但是,没有人提他的事。我也就无从得之。
我到队上一年以后,他死了。队长安排人处理他的丧事。其中有我。他家在一个大屋的一隅,有破旧三间房,一副白皮棺材架在四块土砖上。没有吹鼓手,也没有其他亲戚。他老婆在一旁抽泣。儿子在一旁张望。很凄凉。我们把张信秋抬到了棺材里,他还是和生前差不多的样子,不过没有出气而已。没有换衣服,也没有衣服可换。
要封棺了,不知道谁说了一句:“还要带顶帽子吧”。语气听不出是命令还是关切,真的就是那么轻轻的一句话。有人在他家不知道什么地方,找来一顶旧的蓝色帽子,放在了棺材盖上。“么人同几带起”(谁给他带上?)队长问。
我很注意地观察几位社员,他们都不太情愿地推辞,或者尴尬地笑笑。好一阵,队长轻轻地对我说:你去带吧。
我其实在一旁想了很多,为什么要给这个死去的人带帽子?是当地的风俗吗?是因为他是地主,死了也要带个“帽子”?是他们怕死人?我没有答案。我也学着社员的,苦笑着推辞。这下倒好,一看队长看上我了,大家都苦苦地求起我来了。
我是何许人?他妈地!不就是一地主个狗崽子吗?生产队的人不至于看了我的档案吧!
无奈,拿起那顶旧帽子,伏下身。仔细地端详了死去的张信秋,
“老张,我给你带帽子啊”。
言毕,我将他的头轻轻抬起,把帽子正正地给他带好。
社员们好象也如释重负,急急忙忙地进行下一步的事。
我一个人跑去山边的溪水里洗手,洗了很久。这一回,毕竟是我第一次零距离地和死人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