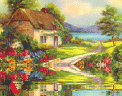连年的八九月的这些日子里,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的每条大街小巷中,总会此起彼伏地响起那种特有的拖音:“哎......葡萄哎......香咧,甜咧......”。这些香咧 ,甜咧的喊声引诱我硬是要去瞧瞧。于是,我老是应声而去,洋洋洒洒地提着许些串串回家。满怀希望地觅回已有远离三十多年哪次之香,那次之甜,不知什么原因每每使我失望。
还是在公元1966年的3月里,那时我正在位于湖南西南边陲江永县当知青。江永县的三月早已是一片郁郁葱葱满绿的世界了。那时的江永县境内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安置着一群群风华正茂的、从长沙省城来的知青。他(她)们都恪守着忠诚、忘我地在那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三月的江永,已是秧田翠绿的时节了。一天早上,我从田里扯秧回宿地吃早饭,看见队里一个叫成君的男知青,在我们全队青年用双肩挑出来的小楼宿舍前的土坪的陡坡坎的半腰处,弓着腰艰难地举着锄头,聚精会神地在刨找着什么。好奇心驱使我走到边坎,对着下面埋头苦干的成君喊道:“喂,你在找什么?”成君立起腰,仰着头道:“你看,这是什么?”我随着他手指的地方看了看,不觉十分的好笑:“哦,你在挖干树枝!”他愣了一下:“干树枝?小傻瓜,到时你就知道了。”他不理会我,又埋头忙他的活去了。我看见用红线缠在一起,约有尺多长的几根干枝正躺在他的脚旁。对他这种有点疯癫的举动,我懒得再理会,就漫不经心地走了。
过了几许日子,一天我路过那儿,无意间看见有根成君刨动的干枝的节骨处附粘着几点白色的、毛茸茸的、还透点绿色的小东西,它们爬在那毫无生气的干枝上,好象有些害怕的样子,显得可怜巴巴的。“咦!”我心里暗暗吃了一惊。在往后的日子,我路过那儿有意无意的都要顺眼看看它们,这些小东西慢慢伸出来了,渐渐地长得有手掌那么大的十几片叶子挤成了一堆。整个矮墩墩的全高不上两尺。早晨叶子舒展着,看上去还显得有些活力,可一到中午就被湘西南的烈日暴晒得焉搭搭,显得要死不活的样子,跟它身旁的那些鲜活高大的野草比起来,这小东西的长相委实丑陋。除了成君一人偶尔弓腰在那儿抚弄关心它一下,再也没有其他人去过问过它了。
大约是八月初的一天吧,我与其他几个知青与成君一道从田里收工回住地,快路过那堆小可怜的身旁时,成君神秘兮兮的对我们讲:“想吃葡萄吗?我请客!”“葡萄?”大家都面露惊诧的喜色。我高兴地大叫:“你家谁来了?”成君不直接回答我的提问,笑眯眯地说:“你们等着。”说着他“咚”的一下跳下坎去,只见他在那焉搭搭的叶子下面拨弄了几下。突然,在他的手里果真捧着两大串紫红色的、晶莹剔透的大颗大颗葡萄,大家的眼都变大了,一个个张口结舌,半天没回过神来。“请吧?”成君幸福地命令道。大家“呼”的一下涌过去围住他,迫不及待地从他手中摘下一粒就丢进嘴里。“哎呀,妈也,真甜啦!哎呀,妈也,真香死人啦!......”那蜜样的甜,那醉人的香啊,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成君,看不出咧,真有你的!”大家边吃边赞美这个平常很腼腆的、不爱言语的、只知埋头干活的人。成君轻轻地说:“这次回家过节时,从省农学院找来的这葡萄种子,听说刚从外面引进,可惜只活了这一兜。“大家兴奋地叫道:“没关系,这么好的东西,明年开春我们将枝条留下,到处都插上......”
可是,知青命运多变,没等到来年种葡萄的季节。每个人都各自奔向那属于自己的路去了。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那兜长着十几片叶子,矮矮丑丑的葡萄却时常在我脑海里闪现。你这兜丑丑的葡萄哟,如今不知可否还安在?

还是在公元1966年的3月里,那时我正在位于湖南西南边陲江永县当知青。江永县的三月早已是一片郁郁葱葱满绿的世界了。那时的江永县境内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安置着一群群风华正茂的、从长沙省城来的知青。他(她)们都恪守着忠诚、忘我地在那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三月的江永,已是秧田翠绿的时节了。一天早上,我从田里扯秧回宿地吃早饭,看见队里一个叫成君的男知青,在我们全队青年用双肩挑出来的小楼宿舍前的土坪的陡坡坎的半腰处,弓着腰艰难地举着锄头,聚精会神地在刨找着什么。好奇心驱使我走到边坎,对着下面埋头苦干的成君喊道:“喂,你在找什么?”成君立起腰,仰着头道:“你看,这是什么?”我随着他手指的地方看了看,不觉十分的好笑:“哦,你在挖干树枝!”他愣了一下:“干树枝?小傻瓜,到时你就知道了。”他不理会我,又埋头忙他的活去了。我看见用红线缠在一起,约有尺多长的几根干枝正躺在他的脚旁。对他这种有点疯癫的举动,我懒得再理会,就漫不经心地走了。
过了几许日子,一天我路过那儿,无意间看见有根成君刨动的干枝的节骨处附粘着几点白色的、毛茸茸的、还透点绿色的小东西,它们爬在那毫无生气的干枝上,好象有些害怕的样子,显得可怜巴巴的。“咦!”我心里暗暗吃了一惊。在往后的日子,我路过那儿有意无意的都要顺眼看看它们,这些小东西慢慢伸出来了,渐渐地长得有手掌那么大的十几片叶子挤成了一堆。整个矮墩墩的全高不上两尺。早晨叶子舒展着,看上去还显得有些活力,可一到中午就被湘西南的烈日暴晒得焉搭搭,显得要死不活的样子,跟它身旁的那些鲜活高大的野草比起来,这小东西的长相委实丑陋。除了成君一人偶尔弓腰在那儿抚弄关心它一下,再也没有其他人去过问过它了。
大约是八月初的一天吧,我与其他几个知青与成君一道从田里收工回住地,快路过那堆小可怜的身旁时,成君神秘兮兮的对我们讲:“想吃葡萄吗?我请客!”“葡萄?”大家都面露惊诧的喜色。我高兴地大叫:“你家谁来了?”成君不直接回答我的提问,笑眯眯地说:“你们等着。”说着他“咚”的一下跳下坎去,只见他在那焉搭搭的叶子下面拨弄了几下。突然,在他的手里果真捧着两大串紫红色的、晶莹剔透的大颗大颗葡萄,大家的眼都变大了,一个个张口结舌,半天没回过神来。“请吧?”成君幸福地命令道。大家“呼”的一下涌过去围住他,迫不及待地从他手中摘下一粒就丢进嘴里。“哎呀,妈也,真甜啦!哎呀,妈也,真香死人啦!......”那蜜样的甜,那醉人的香啊,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成君,看不出咧,真有你的!”大家边吃边赞美这个平常很腼腆的、不爱言语的、只知埋头干活的人。成君轻轻地说:“这次回家过节时,从省农学院找来的这葡萄种子,听说刚从外面引进,可惜只活了这一兜。“大家兴奋地叫道:“没关系,这么好的东西,明年开春我们将枝条留下,到处都插上......”
可是,知青命运多变,没等到来年种葡萄的季节。每个人都各自奔向那属于自己的路去了。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那兜长着十几片叶子,矮矮丑丑的葡萄却时常在我脑海里闪现。你这兜丑丑的葡萄哟,如今不知可否还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