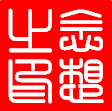路过鲍家,大家都向我报喜,说,长沙的XX中学来招厨工,公社推荐了你。要我赶紧去公社。
这实在是很出乎意料的事。在我的印象中,读书,招工,都是轮不到我的。
虽然七四年夏天也被生产队“推荐”去上学,还到县里参加了体检。后来才听说,这一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全县只有一个名额,当然就不会有我的份了。
至于维尼纶、资氮这类“三线”工厂来招工,就我的出身,是作不得任何非分之想的。
但这时我一点也不动心,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如同被别人推着去了公社。见了知青办的老刘,也见了XX中学来招工的一老一少李、樊两同志。
我说,我不去。就往回走了。
又到鲍家,天已黑尽,我马上被大家围住。
说,好多人都去找了老刘,尽说你的好话,老刘被打动了,下决心:他们两兄妹这回一定要送走一个!
说,招工的老李说,他解放初期就听过你父亲的报告,是老革命,没问题;
说,你不肯去,你妹妹都急哭了;
说,…………
我的脑袋像要炸裂一般。还是说,不去。
我要回去。一个人走了。全然不顾心急如焚、扼腕顿足的同学们。
到十一队,和NL聊了几个钟头,唯有他听得进我的陈述。
由于回城无望,我索性沉下心来,想想我到底还能够为生产队做点什么。此时,队上的育秧、植保等“技术活”已经全是我的事。我也搞不懂,队上的好几个小伙子都比我聪明能干,但他们就是不学这些农业技术,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啊,为什么对自己的事就没有兴趣呢?不懂。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可能懂一点了,人民公社的事其实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
此前,已有知青QD当了七队的队长,HP当了五队的队长,我有想法,有能力,有信心,为什么就不能当十二队的队长呢?到顶山的粮食亩产只有五百斤左右,增产的潜力还很大;到顶山上万亩的山林还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到顶山……
已经后半夜了,我还是坚持要回去。
我必须静下心来,独自面对自己,面对未来。
NL一再挽留,最后也就任由我去了。
临走,我说,我不会去当厨工的。NL默默点头。
这一夜,我想了很多很久。
这一夜,我睡得踏实。
上午被队长叫醒,说招工的樊老师上山来了,正在他家等我。我一惊。但不肯去。队长求我。从没见过他这样苦苦求我。
实在过意不去了,我拖拖沓沓进了队长家。
火塘边,我们三人轻言细语地争论争吵了几个钟头,他俩动之以情,晓之以厉害,……
最后,我崩溃了,屈服了。更可能的是,我其实不堪一击。
我跟樊老师下山去公社办手续。路过十一队,我说,你等等,我非得进去一下。
见了NL,我说,我去。NL的脸一下就白了。
我再也无话可说。我一夜之间就背叛了他!
樊老师要我帮他搞两根好一点的扁担木,他是湖区来的工农兵大学生,那里年年冬天是少不了要挑堤的。在山上,这不难。再杰(队长的弟弟)问我,你自己不带点东西回去?我那里有干的木板子,你自己去选吧。
队长给我五块钱,说,队上送的,你回长沙后买点东西,开了发票寄来就是。后来我用这钱买了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钢笔我一直用了三十多年,直到前几年,实在不能写了,才开始用现在时行的签字笔。
再杰挑着他给我的木板,送我到鲍家。
上了拖拉机,车开动了,鲍家的一位老奶奶扬起手,喊:还要回来瞅瞅哦。
顿时,我泪如泉涌。
回城几年后,我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滔滔不绝,在到顶山作当上生产队长后的“就职演说”,说到激情处,于极度兴奋中醒来,对自己在梦中说的每一句话还记得清清楚楚,还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
○四年回去,那晚在再杰家,大家都去睡了。夜阑人静,我和再杰还在聊天。他关了昏黄的电灯,漆黑中,只有两颗烟头一明一灭。那种漆黑,城市里绝不可能有的漆黑,我已经不习惯了的漆黑。
常想,我真的能在到顶山扎根一辈子吗?虽然我当时甚至有了娶个农村姑娘,在那里安家的想法,看起来还颇有点理想主义的烂漫情怀,但实际上恐怕只是绝望中的奢望罢了。
还有,如果那次不是来招厨工,而是别的什么更“体面”的工种,我还会那么坚决(或犹豫)吗?
我们的青春留在那里,我们的血汗洒在那里,但我们的根真的可能扎在那里吗?!
永远梦里萦绕的到顶山,那真是透彻骨髓、真真切切的剪不断,理还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