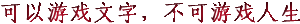走三峡平湖
怎么也按捺不住,我又走上了这条从9岁起走过了几十遭的故道——长江三峡,它实在是那么让人牵挂。
1938年,就读于中央大学的父亲,随南京沦陷后的迁校走入四川,在成都,认识了就读金陵女大同样内迁的母亲,由此,这条长河载入了我们家几十年的风雨岁月。而今年3月,我回到重庆,捧着母亲的骨灰盒,把她安葬在于文革中悲惨去世的父亲的墓地里。一个了却的心愿,结束了这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在长江边七十年生存的历史---因为,几个孩子都走了,远远地离开了这条伤心的母亲河,早就走到天涯去谋生去了。
我知道,安葬完母亲,一旦离开,已近六旬的我,很难再来。我决心登上江轮,再走一遭三峡。
清碧的江水荡着微波而不再流淌,儿时就那么熟悉的江边小城一个个面目全非,汽笛带着回声震荡在峡谷中,江轮很陌生又闯进了三峡。停滞了的思维,竟不知何时过了巴东。高耸的斜拉桥纲索像竖琴一样无声地演奏着蓝色梦幻,这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山间小镇,己发展成一个洋溢着现代气息的崭新城市。巴东以上,江面愈来愈窄,夕阳穿过云层,在大江上打出几个耀眼的光斑。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船尾的沙鸥开始了追逐。阳光中是一片橙黄色的雾霭,倒是重重山影仍然封住了去路。
但是,雾气挡不住我的视线, 我知道, 在江水下,我熟悉的一切都还在那儿。大坝蓄水前,曾不少媒体称,三峡的景观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当然,他们是习惯了向上看:几百米乃至上千米的绝壁,损失几十米又算什么呢?然而往下呢?那些古自以来的存在呢,难道真的是那么不起眼?那么微不足道?
新三峡与往昔的对比,我们损失的,也许只是峡江水涨水落的四季而已。冬天枯水时,两岸的千姿百态岸礁,即那些页岩、砂岩、砾岩褶皱、断裂、扭曲、错位形成的,粗犷夸张而又精细万分的石层线条,我们是看不到了!岸礁上那些钎夫行走了千年的脚窝、洞穴、栈道,我们也看不到了。再高一点,“兵书宝剑”、“牛肝马肺”也都看不见了。即使我抬起头来, 峡谷中更多的几百米高的绝壁,难道不是矮了很多吗?
巫峡中,神女的确是无恙的。她依旧高高在立在峰巅的巨石下眺望,望断归路。而归路却只是一片氤氲的虚无。比如,我曾徒步走过的那条从青石到培石的山间栈道,也沉进了江水,只有几小截的零星片断的山径,还低低贴着水面。当年行走这一段的艰险,现在望过去己如履平川。水波轻抚处,有几叶小舟靠着山壁,一步就能跨上当年险峻异常的栈道。船在巫峡中拉响汽笛,像一声告别的长叹。
船到巫山,夜幕己经垂下了。巫峡入口的新大桥下,巳经是一片烟波浩渺的宽阔江面,似曾相识,一下子让人又想起了烟波浩缈的洞庭。暮色中的小三峡,敞开了一个大口子,一条又一条机动小舟满载游客出峡而来。而在我的记忆中,这里曾是层层叠叠的嵯峨群山,山谷里总是一片幽幽的苍蓝。湍急的小溪深深地切断山与山的连接,涌到一条更加湍急而清澈的小河中。而这条幽蓝的大宁河,怎么也变得如此的波澜不惊? 大宁河就是这开阔的湖口吗?
三十年前,当我从这里“上山下乡”时,大宁河还是一条极为荒凉和沉寂的小河。我们是乘一条拉纤上行名为“两头尖”的小舟,一头扎进大山那种令人孤独的蓝色中的。我还清晰地记得大宁河是怎样在山谷里左冲右突,猴群攀着绝壁上不知什么年代修栈道留下的石孔上窜下跳,纤夫们悠长绵绵的号子带着单调的回声,和着船底磨在河槽上鹅卵石上的嚓嚓声,叠加在哗哗作响的流水浪花中。只有正午时分,阳光才能从那高高的山缝里,剑锋一般地射进深深的峡谷。而眼前的平湖,不觉之间,让我——一个不知归路的游子,心里生出几分隐痛!
船停在巫山,停了多久,我没有查觉。举着小旗的导游把人们带上了船。人们欢天喜地述说着山里的一派清流。没有人知道,大山里是怎样曾埋葬了船舷边一段老知青的青春岁月。
几天过去了,我们顺水东归。落日躲进云层,阴沉沉的夔门中,高耸的瞿塘峡依然锁紧了大江,仍旧是碧波荡漾,只是江水不再追着浪花向东奔流。
过了白帝城,轮船在风箱峡中平稳地驶过,孟良梯下有新砌的朱栏壁瓦的小亭。在右岸,高峡悬岩上见不到那一线栈道了,一树夭挑还开在山径边。而左岸,题刻满壁的岩石, 己贴近了水面。
拾几幅2007年3月的三峡吧--------我走了几十遭的人生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