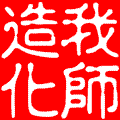去中岳,是82年,我们从甘肃敦煌学习完,回杭州,一路上停了西安,再停就是郑州了.停郑州,是打算去看少林寺,那时,<少林寺>的电影还余威未息,塔林的景致是很有吸引力的.
早上,汽车从郑州出发,走了两三个钟头吧,刚看见太室山和少室山,车就停了.导游说,这是嵩山,去看看吧,半个钟头!
下车,走过一条大概有十来米宽,米把深的干河沟,不多远,就到中岳庙了.不要票,走进去,参观者也就我们这一拨,十来个人,冷寂非常.庙坪内,森森的古柏耸立着,歪斜着,一抱粗的,两抱粗的,无言地叙述着它们的古老.大殿显得有点儿破败,但正是这种破败,使它沧桑满面,气派非凡.我们没看到说明文字,也没看到守庙的僧人,我们只好沿着长满青苔的长廊静静地看着.大殿的外面,长廊的左边,有一个巨大的石椁.(古代的棺材有两层, 并称棺椁,内棺外椁.)以前读<礼记>,里边有”桓司马(人名)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总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石棺材三年还做不好,现在看了这个石椁,才略微明白了一点.中岳庙的石椁精美异常,几面都雕有漂亮的花纹,每面都是一块整石料雕好,再拼合而成.因为它里边还要放棺,所以体积也比较大(当然,比我们博物馆的马王堆的木椁还是小多了).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要做成这么个大家伙,当然是不容易的.嵩山在庙的后面,还没等我们仔细看完中岳庙,导游就在外边喊上车了.不得已,只好往回走,往少林寺赶.
这就是我的中岳之游,惭愧得很,虚有其名而已.
回到郑州,才忽然联想起,我们随便跨过,丝毫也没有注意的那条小河沟,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古书上屡有记载的颍水,它的上游,就是少林寺前面的那条山沟,电影里和尚们提水练手劲的那个地方.当年尧让天下给许由,许由不要,觉得尧的提议弄脏了他的耳朵,于是到颍水中去洗耳朵.碰到巢父牵着牛,到许由洗耳的地方来让牛喝水,听了许由的叙述之后,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弄脏了我的牛的嘴巴!于是,绕过许由站的地方,把牛牵到远远的上游.看,中原就是中原,随便碰上个什么东西,说不定就和我们远古的祖宗扯上关系了!.
我想:我们的祖先称嵩山为中岳,是认为它居天下之中,嵩者,中也!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我们嘲笑贵州的夜郎国君,认为他竟敢问汉朝的使者,”汉朝与它哪个大”,并为此而创造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认为嵩山是天下之中,现在想起来,不也同样可笑吗?是不是要再造个成语,来记录我们的可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