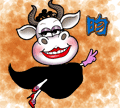以前看过一本描写知青的小说,叫《苍凉青春》,内有一篇描写北京知青后代遭遇的文章,看过有一年了,今天仍对主人公的际遇难以忘怀。今天从网上找出来,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能将它看完。(一次发不完,拟分三次发)
荒原的种子
作者:白描
上篇 逃婚
她叫王杨玲。是一对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儿。
1970年11月27日,她出生在L县一个偏僻的村子。她的呱呱降临,没有给父母带
来喜悦和激动,紧紧攫住他们的只是恐惧和羞耻。在离乡背井、孤苦无依的插队生活里,
这一对青年男女偷尝了爱情的禁果,那一刻的欢愉也许使他们凄苦的心得到了些许安慰,
然而,由此他们却播下了一颗苦难的种子。望着这个孱弱的女婴,他们六神无主,泪水
断线似地滴落在婴儿的襁褓上。
孩子只能送出去,可供这对年轻父母选择的只有这一条途径。下边。等待着他们的
将是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压力,是人们的耻笑、领导的审查和自个无休止的检讨。即使撇
开这些不顾,恶劣的环境使他们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更何谈什么抚养这个弱小的生命。
他们托人为孩子寻找人家,人家找到了,他们顾不得细问,便将孩子送与人。
收养孩子的人家姓王,是一户老实巴交的农民,夫妻俩从未生育过,抱来孩子的时
候男的已经55岁,女的已经47岁。他们探听出孩子的生父姓杨,为了对得起那对可怜人
儿送孩子来世上一趟,他们给孩子取名叫王杨玲。
小杨玲抱进这户人家时尚不满10天。养母自然不会有奶水喂她,好在家里有只老奶
山羊,两个老人每天便从老山羊那干瘪的乳头上捋些奶水喂给她。几个月后,老山羊的
乳头实在持不出什么来了,养母只好把小米压成面,再熬成糊糊抹进她的小嘴里。小杨
玲居然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日出日落,小杨玲一天天长大。她5岁那年,一对北京知青找到养父母的门上。这
对知青便是小杨玲的生身父母。两人早已结为合法夫妻,并且有了一个小男孩。他们终
于熬完了苦难的岁月,在招工招干的尾声里,被招到铁路建设部门,将远远离开这里开
始新的生活,他们来最后看一眼亲生女儿。他们走了,他们的骨肉却要永远留在这里了。
也许他们曾经想把小杨玲带走,只是养父养母不肯放弃;也许他们本来就没有这意
思,把她带在身边,难免总会勾起痛苦的记忆——他们当时究竟持何种想法,至今小杨
玲无从知晓。总之,她留在了农村,留在了黄土高原。
生身父母的工作地点在唐山。真是这对苦难人儿的劫数,1976年初参加工作,过了
半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便发生在他们脚下。之后,有消息传到村里,说那男女二
人同死于地震灾难;又有消息说,死的是女的,男的只是受了伤。无论哪种消息均无法
证实,而事实却很清楚——从此以后,小杨玲的生身父母再也没有任何音讯。
嚼咽着贫寒农家的粗食淡饭,伴随着高原的风霜雨雪,小杨玲长到16岁。
这一年她正上初三。这孩子也许很早就明白她的身世比别的孩子悲苦,从小读书就
很发奋,学习成绩一直在同学中拔尖儿。到了中学,各门功课都优异,对语文则格外感
兴趣,她喜欢看书,喜欢写作文,喜欢对着广袤的高原和空阔的蓝天漫无边际地幻想。
她为“全国中学生征文比赛”写过一篇名为《我与同学的爸爸》的小说,还给山西
《青少年日记》投寄过两篇日记。她暗暗确定了自己未来的志向——当一名作家。
然而,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命运却把她推向另外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终将难以回避——养父养母收下别人送来的一个红包包。红包包里包着她
的订婚礼金——200块钱。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她便会像村里众多的姑娘一样,被
打发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家去,给人家当婆姨,生孩子,然后窝窝囊囊糊里糊涂度过一生。
农村姑娘普遍的归宿她是清楚的,但从来没有把这归宿同自己联系起来。她有点猝
不及防。她哭了,抗拒养父养母强加给她的婚姻。养父养母不理会她。他们需要的是钱,
因为她流泪而抛掉握在手里的钱,那就等于抛掉了过日子的指望,他们不愿听她的。
确也是这样。光阴不催人自老,把王杨玲养到16岁,她的养父已经71岁,养母已经
63岁。这种岁数的老人不可能再在土地上拼气力。家里还有个叔叔,是个精神病患者,
也56岁了。地里的活儿,就靠这个精神病叔叔,想干就胡乱干干,不想干就撒下满世界
乱跑。经济上没有其它来源,就靠土地,土地经管不善,家里早已穷得叮当响,有时连
买盐买灯油的钱都没有,给杨玲订的这个人家,答应事说成先给200块礼钱,订婚席一
摆,除了扯八身衣裳,再给200块,结婚时给多给少虽由男家说了算,但总还会有一笔
数目。老两口抚养杨玲一场,到老来从杨玲身上讨回点补偿,也不枉16年的辛苦。老两
口这么看,村里人也这么看,因而,小杨玲的婚事便订定了。
小杨玲则感到自己被拍卖了。
家里收了礼金,王杨玲还没有见过男方。她哭肿眼睛回到学校,见到老师同学不敢
抬头,像做了什么丢人事一样。她再也没有心思学习,再也不能安静地坐在教室里了。
她哀叹陕北农村的贫穷落后,恨那坑人的封建习俗,抱怨养父养母,同时又可怜他
们。
她为自己的命运深深地感到悲伤。
好多天以后,她见到了给她订下的那个男的。那是个星期六,她刚放学回家,那男
的就扛把镢头进了门,看样子是帮她家去地里干活了。那男的不住地拿眼睛贼溜溜地盯
她。她躲进窑里,不一会那男的也进了窑,坐在炕沿,一边抽烟,一边主动找碴儿和她
说话。他说他给她家干了多少活儿,又说她身上穿的衣服太短,他给她买了新的,过几
天就送来。他说他也上过学,本来能考上中学,但一见上学没出息,就回了家;他在家
不劳动,做生意。但是过了一会儿,又说他在外边搞建筑,跟很多包工头是朋友,有时
候给包工头订合同。他云山雾罩地吹嘘着自己,一听就知道没有几句实话。看着他那灰
黄的脸,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还有边说话边往地上吐痰的样儿,她直犯恶心。
这次见面后,她在学校里写了篇作文——《一个中学生的命运》。她流着眼泪,倾
诉自己的遭遇。她再也不怕老师同学知道自己的事儿,她要把自己的心声,把她的苦恼、
哀伤和悲愤讲出来。老师看了这篇作文,把她叫去,详细询问了她的遭遇。随后,老师
明确表示态度:支持她与那男的解除婚约。
老师的同情鼓励给了王杨玲力量。她向家里提出了解除婚约的要求。
不等她说完,年迈的养父便制止她再说下去。老人眼一瞪,说:“好好的婚事退啥
哩?退了还不得再找?胡折腾个啥?给我安安稳稳的,甭胡思乱想。”
她争辩道:“你们是包办婚姻,我不同意。”
老人说:“包办?父母给女儿瞅人家,咱这里一辈一辈都这样。不要念了几年书,
灌了点洋汤,就给我胡跳腾!”
“我还协…”
“还小?都16岁啦!好,你小,你小,让我和你妈再把你养活着……”老人一生气,
痰涌到喉咙,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上气不接下气的咳嗽。
反抗失败了。王杨玲不光未能解除婚约,反而家里不再让她上学。老父亲认为她之
所以要退婚,都是念书把心念野了。她被强制性地留在家里。学校生活,令人心碎地和
她告别了。
在土地上劳作的重负,开始压在她16岁的嫩肩上。每天,她和那个神经病叔叔到地
里,从早干到晚,当她抱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的时候,仍然不能停歇,家里养着鸡,
养着羊,还有一条瘸腿老驴,她必须经管,她所在的村子地处原区,土地虽然相对较多,
但水极缺,一口井钻20多米深才能见水,村里人吃水都花钱买,4角钱一桶。她家买不
起,只好自己去绞。井绳上拴着两只小桶,绞动辘轳,一只桶上、一只桶下,10多小桶
倒一大桶。井离家很远,她要歇几气才能把一担水担回家。沉重的劳动压得她难以喘息,
她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和父母说话,也不愿意和村里人说话。有时正在干活儿,看见
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上学或放学,心里就涌上一股酸楚的滋味。虽然她已回到家里,
但仍然遏止不住对学校生活的思念。她一遍又一遍回味上学时的种种情景,有些极为平
淡的细节,现在回想起来竟是那么温馨,那么富有情致,那么值得留恋。想着想着,她
便不由得暗暗掉下眼泪。她想找些书来看,但家里没有。一次见邻家窗台下扔着本破旧
发黄的《农家年历》,便借来读,毫无趣味的一本小册子她竟读了一遍又一遍,那上边
的农谚、生活小知识她几乎都能背下来。平时走在路上,只要发现地上有片碎报纸,她
都会拾起,不管上边印着什么,总要细细去阅读。她尽可能地把那些能阅读的东西都收
揽到自己手边,聊以消解精神的饥渴,要不。她的精神就会变得更加空虚、更加痛苦。
那个男的经常住她家跑,每次一来,便开始吹嘘自己,她对他讨厌透了。有一次,
她终于不能忍受,对那男的说:“往后你不要再来了,咱俩的事,最终肯定不能成。”
那男的斜眼看着她,说:“不成?你家把我的钱都花了!”
她大声说:“钱,一定还你!”
她陡然下定决心:即使呆在家里,不能上学,也要和这个男的断绝关系,她绝对不
能忍受和这样一个男人生活一辈子。
她开始寻求支持。她首先想到那位读过她作文的语文教师,可是去找这位教师,人
家能给帮什么忙呢?必须找管这号事情的,比如乡上的干部。她的婚事是包办的,她不
自愿,政府应该出面干涉。这么一想,她便瞅了个机会,跑到十多里外的乡政府。乡干
部听完她的倾诉,头一摇:“乡上不管这种事。”轻轻一句话就把她碰回来,任她再怎
样央求,人家就是不理。她不甘心,不能就此罢休,乡上不行,她找县上去。
过了两天,她对两位老人推说去同学家,从家出来,搭了辆顺路拖拉机来到县上。
她先找到县法院,法院的人说他们只管打官司,她的事算不上官司,应该去找县妇
联或县政府。找到县妇联,接待她的人很热情,但说包办婚姻的事在本县以至整个陕北
都很普遍,妇联只能发文件让全社会来制止这种事,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插手解决。她失
望了,从县妇联出来,怔怔地走在大街上,一时竟没了主意。她不甘心就这么回去,在
县城里转悠来转悠去,最后决定再去找找县政府。可是,她刚踏进县政府大门,就听见
传达室的人一声大喝:“干啥的?”她说明原委,人家没听完,手朝墙上一面挂钟一指,
说:“不看看时间,下班啦,没人!”
奔波了一整天,劳而无获,她只好回家。
不到黄河不死心。过了十多天,她又一次来到县上。
在县政府办公室,她见到一位年轻干部。听完她的诉说,年轻干部让她去找县妇联。
她说县妇联已经去过,具体的事情人家管不过来。年轻干部皱着眉说了声“扯淡”,
沉吟片刻,对她说:“那好吧,你先回去,我给你们乡领导挂个电话,让他们派人去你
们村了解一下情况。”她一再道谢,然后满怀希望回到家里,等着乡上派人来。
过了好多日子,乡上并没有干部来村里。她急了,又找到县政府,办公室那位年轻
干部说电话早已打过,至于乡上为啥没派人去,那就不得而知。她问能不能再打电话催
催,年轻干部摇摇头,说:“再打也没用,这种事,乡上想管了就管,不想管了谁也没
办法。”说完,扔下她匆匆去办别的事情。
她怏怏走出县政府大门,眼泪止不住籁籁流下来。再也没有别的去处可找,再也没
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她原指望政府部门能助她一臂之力,帮她挣脱身上的枷锁,看来这
个想法落空了。真是求天不应、求地不灵,难道她真的就该受那可恶的命运的摆布么?
在热热闹闹的大街上,人们好奇地盯着这个泪流满面的年轻姑娘。她不愿意引起人
们的注意,走进偏僻的小巷。躲过杂七杂八的眼睛,她哭得更伤心。哭着哭着,她突然
想到了死。死?对,死也是一种反抗,也能表达她对命运不屈从的决心!可是……她死
了,对年迈的养父养母打击该有多大?不错,她怨恨他们为她订亲、逼她退学,怨恨他
们脑筋陈旧落后,但他们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大,容易吗?他们也怪可怜的……她突然又
恨起亲生父母来。她本不该来到这个世上,既然他们荒唐地生下她,就应该负起责任,
尽到自己的义务,然而他们却自私地一走了之……眼下她该怎么办?还回到家里去,等
待着某一天去给那个脸色灰黄、满口谎话的男人当妻子?不,纵然死她也不愿意这样。
她突然想起一位同学在县医院当护士。能不能去找这位同学介绍她当护工?洗被褥,
打扫卫生,挣下钱就去外地。去哪儿,不知道,反正先离开这儿。也不能亏待了养父养
母,她会给他们寄钱……主意一定,她便抹净眼泪,奔县医院而去。
谁知到了县医院一问,她的那位同学早就回家不干了。她软塌塌坐在医院走道的长
椅上,泪水一下子又涌出来。
“女子,你哭什么?”忽然,一个讲普通话的人问她。
她抬起头,见是一个女的。三四十岁,手里提着药,像是来看病的。这女的眼睛里
充满了真诚。从声音她判断出这人是位留下来的北京知青,不知为什么,一种奇妙的情
感使她再难抑制满腹酸楚委屈,“哇”一下哭出声来。那女的在长椅上坐下,抚摸着她
的肩头,说:“别哭,说说你有什么事?看我能不能帮你。”于是她一边哭,一边把她
的身世遭遇讲了一遍。那女的听罢,眼圈儿红了,安慰她说:“我也是个北京知青,县
上还有好多我们这帮人,你是我们北京知青的女儿,我们会替你想办法。”她告诉杨玲,
她叫祝萍,在县农行工作。她说她要先和县上的北京知青商量一下,叫她过几天再来找
她。她把杨玲领到家里认了门儿,还留杨玲吃了顿饭。
十多天后,杨玲又来县上,再次见到了祝萍。祝萍高兴地告诉她,她的事儿县上一
伙北京知青商量后,决定直接向梁县长反映,因为梁县长也是位北京知青。这一招果真
管用,梁县长当即表态说他要干预这件事情。“解除婚约不成问题了”,祝萍轻松而又
愉快,一把拉住她,说:“走,大伙都想见见你,往后你该怎么办,大伙还得商量商量
哩。”
杨玲心里激动,鼻子发酸。她随着祝萍,见到了五六个在县上工作的知青叔叔阿姨,
他们个个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她、疼她。感受着他们亲人一般的体贴抚慰,她索性
放声大哭,哭得好不伤心。
这次她没有回家,第二天,她怀里装着叔叔阿姨凑起来的钱,乘车奔向延安。大批
北京知青离开延安后,地区劳动人事局下设了个知青处,负责处理知青遗留问题,他们
鼓励她去找这个机构。她是知青的女儿,养父养母已那么老,实际上她已无依无靠,往
后的事,知青处不能不管。
到了延安,天正下着大雨。找到知青处,杨玲已是浑身透湿。正好知青处有一位叫
余风云的阿姨,是北京知青。听完她的诉说,余风云先把她领回家里,从里到外,替她
换了身干净衣服,并留她在家住下。随后,余风云便为她的事跑开了。
知青处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他们感到棘手,必须向上请示汇报。事情拖下来了。
王杨玲的身世及遭遇很快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中传开。他们纷纷到余风云家中来看她。
地区建筑公司陈铁生、刘学军夫妇执意把杨玲从余风云身边带走,他们决定收养这
个可怜的姑娘——这棵北京知青伙伴留在黄土高原的可怜的根苗。他们在家里为她支了
床,让她安心住下,并交给她一把家里大门上的钥匙。他们知道她渴望学习,喜欢读书,
第二天,就领她去新华书店,由她在书架上挑循…仿佛进入梦境,在人世间,王杨玲没
有想到自己竟能领受到这份温情和爱意,她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她的泪水止不
住一遍又一遍流淌……只是流泪,没有语言。
……
感谢上苍,王杨玲,这个不幸的姑娘,最终成了延安北京知青共同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