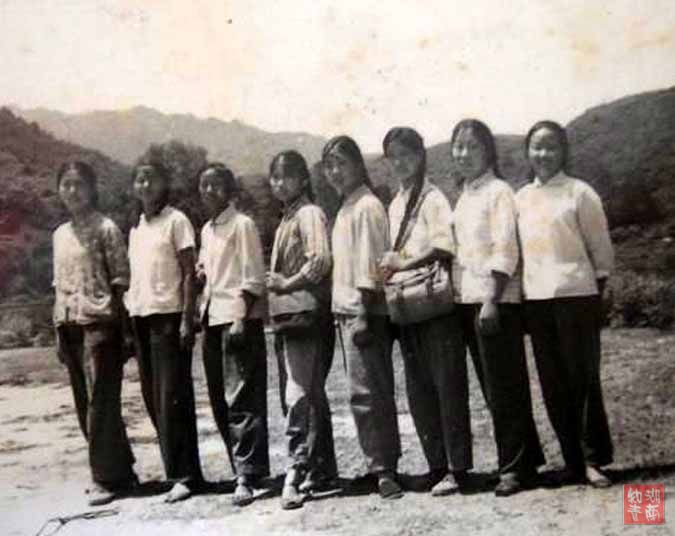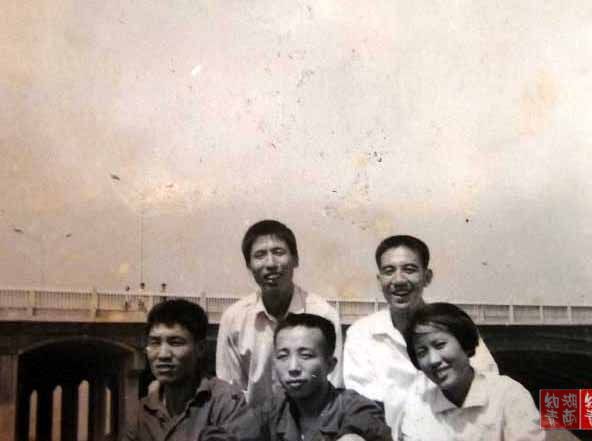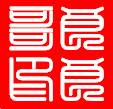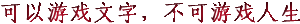铺口知青百态
(一)两肋插刀
“狗毛”是我们铺口的知名人物,个子较高,单瘦,说话诙谐风趣,逗人喜欢,走到哪里都深受知青欢迎,常被邀请到各知青点串门。他哥哥是我的同学,与我同一个大队的,小名“羊毛”,作为他的弟弟自然而然就被称为“狗毛”,他俩兄弟不在一个队上,“狗毛”在邻近的一个大队里。
一次“狗毛”外出串门回来,搭乘一辆轮式拖拉机(铁牛--55型),说是搭乘,其实是站在拖拉机驾驶员的后面,开拖拉机的是一位老知青Z,费了许多周折,好不容易才被公社选上开拖拉机的,所以他开起车来兢兢业业的不敢违章,那时的拖拉机就光突突的一个机头,就只有驾驶员的的一个座椅,规定机头上不许搭乘傍人的,当拖拉机快开到公社时,“狗毛”就要下车以免被公社干部看到Z的违章,他看到离地面不高,速度不快,就径直朝路边跳去,但贯性将他摔倒在拖厢轮子下,他自己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时,拖厢的一边轮子就从他胸脯上滚了过去,好在拖厢里只装了两包水泥,拖厢辗过后,他一轱辘从地上爬起来,伸手踢腿,活动还自如,只是胸口有些痛,这才回过神来,好险啊!捡回一条命来。
这时Z司机也从反光镜中看到他栽倒在拖厢轮下,来个紧急刹车,脸色发白的跳下机头,向“狗毛”奔来,连声问道:“压哒哪里?压哒哪里?要上医院去看不?”“狗毛”稍微缓回一口气后,勉强站直,强忍住痛说:“冒得事,冒得事,你走你的,你走,”“真的冒得事咯,那我就先走了,有事就喊我。” Z司机看见“狗毛”还能站起来,以为问题不大,帮他拍掉身上的灰,安抚了几句,才忐忑不安的离开。“狗毛”微笑的站在路傍,还优雅的向Z挥手告别,等拖拉机走得看不见后,他才躬起背,用手揉着胸脯,慢慢的朝队上走去,其实他伤的并不轻,他怕这事故会砸了Z开车的饭碗,所以才强忍着装作没事的,想起刚才那一幕,他还是很后怕的。
他蹒跚的走到他哥哥“羊毛”的队上,胸脯痛得更厉害了,还咳出血来了,“羊毛”觉得不妙,当即送他到靖县人民医院去治,到了医院,医生一照片子,发现压断两根肋骨,就收下他住院治疗,但医院又没有办法将肋骨复位,只能呆在病房里干躺着。
“狗毛”是个闲不住的人,住院了也如此,白天在医院四处闲逛,到各病房串门聊天;晚上,偌大个病房十几号人都在听他讲故事和瞎扯,“狗毛”的口才好,不乏幽默生动,妙趣横生,一讲就是大半个通宵,尽欢才散。那些病友也喜欢听他讲,听到有趣时,还不时发出哄堂大笑,常惊醒了隔壁的病人。对此,医院很恼火,说他们半夜吵闹,指责他扰乱了医院正常秩序,对他下了逐客令,说这伤躺在家里也能治的,就将他推出院门。
“狗毛”没办法,只好回到队上疗伤,队上的社员看到这情况,帮他出主意,找县城的专治跌打损伤的土郎中,“狗毛”那时也心急乱投医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同意去试试。于是,他们队上的人就带了“狗毛”到县城找了个土郎中,那土郎中要“狗毛”脱去衣服露出胸脯后,他直接用手指钳住“狗毛”塌陷的肋骨,硬生生要将它复位,痛得“狗毛”得眼睛鼻子皱成一坨,嘴巴咧得一边,连声叫痛,那人不为所动,钳住不放。好在“狗毛”下放后专长骨头,没能长肉,胸脯象洗衣板似的,根根肋骨棱角分明,给衔接术创造了有利条件,居然让土郎中给拉复位了,这时的“狗毛”已痛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说也奇怪,肋骨复位后,回队上吃了两付土郎中开的药,休息了一个多月,就恢复了,又精神抖擞,满面春风的出现在铺口的场上,大家见到他,都拍着他的胸脯说:“作古正经的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啊!’”
(二)印刷品
“Y哥,你家里又给你寄报纸来了。”Y哥从同伴手中接过一根卷得象根杆面棍似的邮件,撕开包在外面的纸,果真是两张长沙晚报,摊开一看日期,竟是一个多月以前的旧报纸。
Y哥并不急于去翻看报纸的内容,却把报纸摊开直指中缝,把眼睛憩在中缝看,憩得鼻尖都快顶到报纸了,原来报纸的中缝写有字句,六十年代报纸的中缝是没有广告的。Y哥一字一句的仔细阅读起来,这些字是他母亲写在上面的,字字句句都是对Y哥的挂念和叮嘱。
Y哥家里本就负担重,65年Y哥带着弟弟又下放靖县,又给家里生活增加不小的困难了,家里一分一厘钱都要省着用。那时,寄一封平信要8分钱,而寄印刷品,不超重的话只要3分钱,所以Y哥的母亲就想出了这个省钱的点子,每次写信给Y哥时,先找来两张旧报纸,把报纸的中缝空白处当作信纸,把对儿子的思念都写在中缝里,为的是一次可节约5分钱。
起初,同组的知青还以为Y哥的母亲关心他的政治学习,寄报纸给他看,让他了解大好形势的,后来发现了这其中的秘密,都感叹他母亲的艰辛,用心良苦。如果信写得太长的话,在一个中缝里写不了,就写到另一张报纸的中缝里,有时中缝都写满了,还写的报纸边框的空白处。所以,常见到Y哥在读信时,将报纸翻来覆去,一会儿寻到中缝看,一会儿憩到边框上。
在她母亲的信中,几乎每次来信的最后都要提到Y哥的眼镜:“儿啊,要爱惜好眼镜,莫碰烂了,打烂了就冒得钱配啊!”Y哥高度近视,戴着一付厚厚的眼镜,看东西都要憩得鼻子尖前。上世纪六十年代时候,配一付眼镜要二十来元,是一般工人的大半个月的工资,在当时是一笔大的开支,所以,他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就是莫把眼镜搞烂哒。Y哥也确实百般爱护眼镜,但做农活总免不得磕磕绊绊的,时间一长,他那付眼镜架上緾满了胶布,甚至连眼镜片上也粘了一小块胶布,到我们69年下放时,看到的就是那付伤痕累累的眼镜。
与Y哥一道下放的还有他弟弟,我们习惯称Y弟,Y弟不是附中的,身体和性格都与Y哥相反,身体结实,不喜多话;而Y哥是斯斯文文的一副书生摸样,讲起话来滔滔不决的。两人下放在一个组上,本应是相互照顾的,但到了后来,实在太困难了,两兄弟就分灶吃饭,各搞各的,过日子到了这种地步,在我们外人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现在Y哥可好了,回城后,先在一个企业的子弟学校任教,后退休回长,被长沙东边的一所学院聘请教学,享受副教授待遇。前不久见到他时,他正下课回来,他手中夹着一叠书和讲义,鼻上架着一付高级时髦眼镜,上面没緾胶布了,昂头挺胸的,颇有学者风度。
(三)铺口第一居民
铺口公社在文革时实行全民皆农,将镇上的为数不多的几户居民全部下放到附近两个生产队上去了,镇上没有吃国家粮的居民了。
在我们下放的这批知青中,有一小青年,还只15岁,为了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也跟着附中的哥哥姐姐们来到广阔天地的铺口,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没经过职业培训就让他上岗,对贫下中农分派的工作难以胜任,队上发给他的津贴只是维持在当地最低的工分水准的七分工。他时常被生产队派去修公路、水库的,长年充当生产队的“驻外大使”。他舍其家,专心在外,长期不能归,自留地上自然一片荒芜,他对外称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实属无赖。
回队后,他出工的机会也不太多,主要是没有合适的工作给他做,加上他的社会活动较广,需占去部分出工时间,一年的所做的工分只相当于一个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到年底分红时一点点工资还不能兑现,难以维持下年的生计。为了维护贫下中农的威信,他没把这劳资纠纷向外界宣传,只是汇报给在长沙的父母亲,向他们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的申请,他父母亲都是老革命,非常理解他的动机,为维护铺口的社会和谐,按时给他发送生活补助,他就用这些补助到公社粮站买米,到场上买菜来吃,俨如吃商品粮的居民,因此,老知青们授予他为“铺口第一的居民”的称号。
他虽戴有“铺口第一的居民”的桂冠,但生活一直简朴,早在那个七十年代初,他就注重当地的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他不砍柴的,烧的柴都是在路边田边捡的枯枝,捡一大把回来可以烧两三天,节省了能源并保护了排牙山的森林植被。到后来,为了防止了大气污染,减少烟雾烟尘,他连柴都不烧了,改用柴油小炉子,不敢说在全靖县,在全铺口算是第一个使用柴油炉的人了,够傲的。
那时,他就意识到要节约用水了,看到村民们洗衣洗菜都使用井中的矿泉水,他很心痛,几天才挑一担水来用,实在没水了,就到房东缸里借一点水,以解燃眉之急。他吃菜除了到场上买的外,还注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下田劳动时,会收集一些种在田埂上的黄豆荚,剥开后炒着吃,以补充身体里蛋白质的需要,稻田收割前要放水捉鱼,他顺便截留两条藏在裤口袋里,中午又成了一碗鲜美的鱼汤,但贫下中农的菜他是坚决不动的,保证了铺口一方净土和社会的稳定。
他还是铺口的知青社会活动家,常走村串户,到各知青点去体炼生活;他侠义心肠,爱打报不平,为了维护知青的利益,他多次挺身而出,不畏强权,受到知青们的高度好评;他还乐施好舍,常高朋满座,到他房里有宾至如归之感,所以, 这“铺口第一居民”的头衔,他是当之无愧的。
(四)气鼓
“气鼓”是我们大队的知青,他原是1965年下放在桂阳县的知青,1969年初,他附中的哥哥下到了靖县,他就从桂阳转到靖县投靠他哥哥来了,他两兄弟都少与外界接触,埋头在队上出工。他不是附中的,知青对他都不太熟悉,他小学与我同学,所以我认识他,见面还能打声招呼,但没有多话讲,我以为他是不爱说话的。他哥哥个子较高,脸较瘦,文弱谦和,他却比哥哥矮,胸脯厚实,腰杆子板硬的,头象热水瓶塞,一双眼睛鼓瞪瞪的,他走路的姿势很特别,是鼓着腮,圆睁着眼,一副威猛的样子,仿佛气胀气鼓似的,我们组上的胡健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气鼓”,这个名字很形象,一下在我们铺口传开了。
“气鼓”因做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在铺口知青中一举成名。那是1972年年底,从公社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气鼓”被县公安局逮捕,罪名是里通外国。听到这消息后,我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一个不喜欢吭声的人,竟然会里通外国?我和他在金麦修水库时,同吃同住同劳动达两个多月之久,从未听到他讲过半句对现实不满的话。
不久,从他们队上的知青那里打听到,事情是真的,他的确被抓走了。详细情况是这样的,靖县公安局截住了一封发往香港的信,收信人的地址是敌台公布的地址,公安局一看信的内容,就知道是知青写的。信是在藕团邮局发的,于是公安局就盯住铺口、藕团、新厂这一条线上的知青,逐个排查。我那时肯定也是被列为重点的怀疑对象,因为我的阿舅们在香港,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可能是通过查档案对笔迹怀疑到了“气鼓”,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后,还要找到证据,公安局在生产队策划了一场出工,让队上把知青都安排上排牙山做事,中午不能回来。他们一走,公安局的就进了“气鼓”的房,仔细搜查,没多费工夫,就找到了证据,枕边的那台半导体收音机显示的频率,正是那敌台的频率,他头天晚上还在收听敌台,抽屉里的信纸也与那封信里的相同,有了这些,就可以结案了。
下午,“气鼓”他们从山上回来,“气鼓”看似象个粗人,其实心细,一进房就发觉有人动了他的东西,马上警觉了,联想到往境外寄的那封信,他不免害怕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立刻收拾一点钱和粮票,不辞而别,往县城方向走去。但他已被监视了,还只走到官团大队就被抓住了,送到县里,给判了七年徒刑。
当时,知青都在谈论他,说他不想事,那种信怎么能写?那地址早已在被公安局盯上的。说他不想事?他又晓得这信在铺口不能寄,要跑到藕团去寄,如果他还想得远点的话,丢到县城的邮筒里,那案子就冒得这么快破了。以后又听说此案不算里通外国,是反映情况,属错判,解除徒刑前释放,仍回到生产队上。那信里中究竟写了些什么?他没对外人说过,大家都不知道。几年后他也搭上了知青返城的最后一班车,回到了长沙,安排在河西的一所重点中学当校工,前几年就内退了。
(五)不对称
我的几个同学结伴也来到靖县,比我们晚来一批,公社把他们分到离公社最远的林源大队,离铺口二十里地,与藕团公社打隔壁,69年年初,我们附中下到铺口的知青中,一共只有两个知青组分配到林源,就有一个是他们的小组。他们的组上有五人,全是男丁,个个老实巴交。
下到生产队后,队上对他们还是比较欢迎的,凭空增添了五个强劳力。他们也较快的与社员打成了一片,融合到了他们中间,社员家中有什么事也都喜欢请他们帮忙,不把他们当外人,他们也从不推辞。
靖县管办白事叫吃豆腐或吃烂肉,队上社员家有办白事的来清他们,他们二话不说就去,借此可改善一下伙食,五条汉子,安排给他们的是挖洞,抬棺等重活,他们也不在乎。他们都是湖大、师院的子弟,在家时莫说冒搞过,连看都少见,见了这档事躲都来不及的,如今却参入到其中,无所谓了
他们队上办喜事需接亲,最喜欢请他们去,五个人换上学生装,一崭齐的,都是长沙大城市里来的,要气派有多气派,给男方增添不少的面子,但他们说话不懂忌讳,学校没教过,也闹出过笑话。有一回请他们去接亲,上午在男方家里挨到中午才喝上一碗了桐米茶,到了女方家也只草草的填了一下肚子。饭后他们各挑起嫁妆就往回走,F同学挑的是一担水桶和一个脚盆,不论他怎样摆放,都是一头重一头轻的,担到肩上是一头高一头低的,他边走边连声埋怨“咯不对称呢,连不对称哒。”女方队上看热闹人听到后放声笑,女方的母亲听到后更是气鼓鼓的,嘴里就“剁脑壳的,短命崽”的骂起F来了,F才知道讲错了话,挑起那担不对称得嫁妆飞快的跑了。
(六) 执著的人
在我们铺口的五星大队有这么一位老兄P,他有一个不雅的称呼,叫“屁袋子”,考证这外号的来由,可能与他的消化系统功能欠佳,排出气体多有关。在铺口讲起他的大名,很多人都不知道是谁,但一提起“屁袋子”这个外号,多数知青都知道了,就是五星大队那个以执著据称的人,并且都还能说出他的一二件趣事出来。
P老兄的性格的确有点古怪,按照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非常有个性。他特别固执己见,凡经他认定的事,非要按他的想法去做不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憨劲十足。不知是他看人不来,还是天生孤傲,总之个不愿搭理人家,习惯独来独往,成了孤家寡人,下放不久,他就单独一人开伙了。
在靖县第一天,当他得知他要去的五星大队下偏坡生产队,是地处在马路边上时,他先是失望了,然后愤怒起来,说马路边不算山区,他要去的是真正的山区,要求到大山里,不能满足这个愿望话,他就绝食。在校工宣队苦口婆心的劝解下,他才不情愿的去了该队。
他们那个知青小组有十人,P老兄是年龄最大的,有23岁了,其余九人都是二十岁以下的小弟弟小妹妹,这九人在学校里全是学俄语的,惟独他一人是学的是英语。初到队上,他给本组知青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在卖弄他的英语,其实这是一种误会。读英语对他来说已是一种习惯了,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在那个年代里,我们的课本早就当成废品买了,而他却把英语课本带来靖县了。他念英语不分场合,不看时间,不管有无有人在场,有时是大声朗读,有时又是自言自语似的,在田间做农活时,他的嘴也不歇气,念念有词的在背诵着英语单词。刚开始,社员还觉得惊诧,后来看习惯了,也就不加理会了,只是怀疑他脑子里是不是有毛病。因此,他们组上的人也对他有看法,无人与他合得来,久而久之,都渐渐的疏远了他,他也离开知青组独立门户了。
他单独一人过上了日子,他也不在乎,一次他病了,两天没出工,两天没进厨房,两天没见他人影,社员担心他是不是出了问题?小心的推开他的房门去看望他,发现他盘腿坐在床上,两手放在大腿上,手心朝天,垂眉屏息,有些象庙里的和尚在打坐。社员没见过这架势,忙问他是不是病了?为什么两天没去做饭?而他却要这社员出去,莫吵他,说他正在练气功,弄得这社员哭笑不得,饭都冒得吃,还练么子气功。
在铺口,流传P老兄最多的故事,除了念英语外,就是他老兄砍柴的趣闻了。别人上山砍柴都只带一把刀就行了,他除带刀外,还要携带一把锄头,为什么呢?他砍柴时,一点都不浪费,将树干砍掉还不够,还得将树蔸一并给挖了回来,社员都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理直气壮的答道:“根也可以烧的,不挖出来烧可惜了”,社员鄂然。还传说他赤手空拳弄断一根碗口粗的树回来过,有人说是用石头将树砸断的,也有人说是他摇了两个钟头把树摇断的,可能二者皆有之,这壮举终究无法得到确认,难以令人置信,但一讲出是这老兄所为,人们又似乎认可。他为大家所认识是在石冲水库工地上,他运土很特别,不用肩挑的,一只手提一箢箕土,爬坡快步如飞,美名为练手劲。休息时独坐一处,闭目练气功,他的气功已练到有一定的功底了,在那人声噪杂的水库工地上,他似处于无人之境。
还有,当年大队派给队上一个去巴塘园艺场的名额,队上看P老兄一人过日子无负担,就把名额摊派给了他。在巴塘园艺场里,P老兄每天起早床,带上英语课本,爬到园艺场的后山上读一阵英语,再回到食堂里吃早饭,即没影响到别人,也不要自己动手做饭,他在园艺场过得很自在。只有一点不如意的,口粮要自己回队上去拿,巴塘离他们队上有二十多里,跑一次也蛮辛苦的。正好,有从巴塘园艺场出来的老知青,转到了木山大队,他的口粮还保留在园艺场里,也要时时来背粮,木山大队距巴塘更远,有三十里地,但到五星大队的下偏坡只十里来地,于是这老知青找到P老兄,提出他俩交换口粮,P老兄在园艺场吃这老知青的口粮,老知青就到P老兄队上领取P的口粮,这样,P老兄就免去背粮之苦,老知青也要少跑二十里路,对两人都有利,这样的好事P老兄却不肯干,他一句话就回绝了老知青,“背米也是一种锻炼,我愿意。”怔得老知青半天说不出话来,连连摇头,觉得不可相象,铺口知青中竟还有这种人。
七十年代的后期,他到了长沙某化工研究所当门卫,他父亲在该所当领导。一天,所里要传达重要报告,规定八点钟上班时间一过,就关闭大门,不许人进出。他忠实的执行,按时将大门关闭,偏偏他父亲有事迟到了,被关在门外,任凭磨破了嘴要他开门,他就是不开,他父亲站在门口只摇头苦笑,还是办公室主任来了才解了围。他这是六亲不认,还是秉公办事?这事谁也说不清的。
我总觉得此人不是平常之辈,他思维方式超越了我们,他能预见到将来的事,他在靖县执著的苦练英语,谁也没料到十年后英语人才成了抢手货;他执著的修炼气功,八十年代后气功浪潮席卷中华大地,这一切都显示出他有超前的意识,只是不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还被人们误解成脑子有毛病,生不逢时,是他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