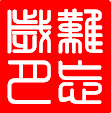失手
我在靖县有过几次失手,69年上山砍柴,失手砍到左手手背上,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我自己的白肉外翻,至今还留下一道疤痕;71年在金麦修水库打炮眼时,失手将大锤砸在扶钢钎的同伴手上,换个位置,同伴也失手砸到我手上,青了一块,肿了好几天。但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失手害了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一只小鸡,现在重提起还于心不忍,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这里有必要先将我们知青组的情况作一番介绍,我们八人(五男三女)原都是下在一队的,二队没来知青,大队为了平衡,将我们四人(三男一女)调剂到二队,一二队都在一个团子里。分成两组后,相隔不远,我们天天打照面,仍然常来往。下放二年后,招工先后走了四人,每组都剩两人,一队留两女生,我们这队就剩我和小h。我不会做饭,就厚着脸皮去一队女生那儿搭伙,她们收留了我,我就主动干一些砍柴,打米,担水等较重的活,她们煮饭种菜搞内勤。那时,她俩都当上了大队的民办教师,放学比我收工时早些,所以我收工回来就有饭吃,凭这点我就很满意了。
与女生搭伙是有好处的,女生常在家,内勤有保障,至少菜有人种,我看到清一色男知青的小组,菜都没得吃,因为男知青常被派出当民工,自留地的菜没人种,种了也没人管理,所以无菜吃。他们羡慕我有菜吃,又有人煮饭。话说回来,我们配合还默契,我也只是吃饭时过来,呆在厨房里,吃完饭就回我二队的住处,不越雷池一步。
第二年夏天,又是青黄不接时,主要是没油了,她俩趁学校放暑假回长探亲,顺便弄点猪油带来。她们一走,我又得自己做饭,饭还好说,早上就把三餐的煮了,中午只需挖一团冷饭放锅加水一煮,就行了。靖县的食俗与长沙的不同,早晚吃干的,中午吃稀的,我也入乡随俗,中午吃起了稀饭,剩下的晚上炒热吃。但菜不好办,没油更伤脑筋。我借买喷雾器零件的机会,到了县城菜场里,看到有长沙产的什锦菜卖,这菜不用下锅,正好对付中午的稀饭,就买一斤什锦菜,用纸包着带了回来。吃了两天就觉得不对劲,感觉到嘴边有东西在爬,用手抓下来看,是条小虫,厨房里光线暗,看不清,拿到门口一瞧,我的妈呀,是条米粒大小的白蛆,再把碗端到门口看,什锦菜上爬了许多小蛆,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还不知我吃了多少进去了。可能是我买的时候这菜就有问题了,当时没在意,买回后就敞开放在碗柜里,大热天的,不出问题才怪呢,赶紧把什锦菜倒了。
因碗柜里也有蛆,我得清扫一下,在清扫中,我找到一个酒瓶,里面还有半瓶子油,闻不出是什么油,管他的,吃了再说,晚上就用它炒了菜,炒出来的菜还是挺香的,口感还可以,吃下去当晚就见效了,肚子庝,不停的跑厕所,连换了两条裤子,一晚都没睡好,怀疑是什锦菜的问题,还是这油的问题?后来听说,这是油是桐油,她们一队分的。
一队知青组的住地,也是我到二队之前住过的地方,是在一栋仓库里,男生住楼上靠南的房间,女生住楼下北边的小屋里,厨房建在女生的门口,占住了仓库前面坪的一角,厨房的门口正对着仓库门,这块坪是一队社员的活动的场所,常聚集着社员,也是各家各户到井边担水的必经之路。我们刚来时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注视中,到了吃饭时,坪中时常弥漫着我们厨房里饭菜的香气,令他们吞涎不止。这里也是猪、鸡、鸭活动的场地,仓库的南边是牛栏,天天有牛从门口经过,所以,我们的门口常常有牛屎猪屎的,鸡屎更不用说,都拉到了我们的厨房里来了。当时队上给我们建厨房时,就考虑方便我们养鸡,将厨房的木门留下一个洞,可以让鸡进出方便。可是,我们无力养鸡,倒方便社员的鸡进出,弄得厨房到处是鸡屎,很烦人的。
现在回到正题上来,当她俩回长探亲后,这厨房交我接管了,鸡们就光顾得更频繁,它们闻到我锅里留有饭,就在灶上,锅盖上到处折腾。还有,我吃完饭后当时不洗碗的,堆在灶上留到晚上做一块洗,这些碗也就成了鸡们的目标。所以,灶上、锅盖上、甚至碗里都有鸡屎,每当我一进厨房看到它们,气不打一处来,赶得它们鸡飞鸡叫的。这时,住在厨房后面的一位老婆婆,常坐在她家门口纳着鞋底,就咯咯的叫唤鸡了,那意思好象是,我家的鸡,赶鸡也要看主人啦。我只好忍声吐气,清它们让出厨房。
那个中午,我照例先请出鸡们,坐下来默默地烧火热饭,也就是一勺水,一团饭扔在锅里煮。这时,一支胆大妄为的鸡又踱了进来,事无忌惮的跳上灶台,我不出声,手拧紧吹火筒,看它到底想干什么,只见它引颈朝热气腾腾的锅里探望,头一摆一晃的,我趁它耵住锅里那一瞬间,一吹火筒扫过去,正巧扫在鸡头,它一声不吭的倒在锅边,险些掉到锅里去了。我一看出了鸡命,吓得一身冷汗都冒出来了,那老婆婆知道后,全家都会与我过不去的,得赶快燓尸灭迹。我找了一个挎包,捡起死鸡塞了进去,不料这鸡竟活了过来,叫了一声,并挣扎着,吓得我手慌脚乱,顿时没了主意,还没等它叫出第二声,慌不择手地抓住鸡脖子一拧,它不吭声了,这回真的死了,刚才那一吹火筒只是把它打晕了,早知道是假死,我何必弄得如此紧张?这时我有种负罪感,我至今还没伤过生的(除苍蝇、蚊子、偷油婆外),我连鱼都不剖的,现在居然杀鸡灭口,真是难以想象。有人说,人在情急之中会做出不可思议的举动出来,经过这事后,我信了。可能一些人的犯罪也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
死鸡是送到别的知青组那儿处理的,看看外面没人,我提着挎包就溜了出来,鸡虽然只一斤多点,但我提在手上如同铁砣般,我还不时的捂着挎包,生怕它又活过来,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还好,社员家都在吃饭,没人看见我的出走。我一溜烟的跑到三里外的王家生产队,找到吴元龙,他两口子还没吃饭。献上鸡后,女主人立即烧水钳毛,鸡很快烧好了,女主人手艺不错,虽然这鸡没有放血,但味道很好,是真正的土鸡,也可能是这段时期我吃多了红锅菜的缘故,这鸡确实很好吃,只是骨头多了一点。吴元龙这人很有意思,他不吃鸡,说是看到那鸡皮疙瘩就不敢伸筷子,我也不吃鸡皮的,但我吃去皮鸡肉,这点我比他强些。
“独鸡宴”结束后,我匆匆道别,要赶回队上出工,以免生疑。晚上收工后,我提心吊胆回到厨房,不出所料,老婆婆来找鸡了,咯咯咯的唤鸡,围着我们厨房转,不时的朝我们厨房里看一下,并没问我,我作案现场早已收拾清了,不留一点痕迹,我也装做懵懂的样子,专心做我的晚饭。她不停的呼唤着鸡,直到天完全黑下,才失望的回家,那悲切的唤鸡声一直在我耳边萦绕,搅得我一晚没睡好。
第二天早饭时,我到厨房去,就看到老婆婆站在坪里骂:“那个剁脑壳的,挨千刀的,短命崽偷了我的鸡,”骂声始终伴随着我做早饭,吃完早饭后,我匆匆出工,迅速离开这是非之地。那老婆婆连骂了三天,这三天我度日如年,她的骂声,使我头皮一阵阵发麻,直至现在,只要一听到“剁脑壳的,挨千刀” 的,我就无意思的缩颈根,落下了这“禽流感”的后遗症。
说实话,那鸡不幸落人我的毒掌,并非我本意,的的确确是失手误杀,但没有人来证明我实属误杀,我也没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件“谋杀”,吴元龙两口子除外,他俩属“销赃”,是我把他俩口子连累了。我们组上那两位女老师回来后,我也没跟她们提过此事,她们是正经八百的,怕她们知道我这劣迹而被驱逐出伙食团。
我一次一次的找理由为自己辨解,是失手误杀,不是偷鸡,但一次一次的又被否定,当发现这鸡活过来时,为什么还要将它卡死?为什么还要把它吃进肚里?难道这也属“失口误吃”?难圆其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再次反省这“失手”案,因吃进到肚子里去了,性质就变了,实属偷鸡,这是我在靖县的唯一一次的越轨。
肥皂风波
在我们知青组中, 竟有一位是北京女八中的女生,此人从小在北京亲戚家生活,在北京上的中学,属67届初中毕业的,因父母都在长沙工作,下放时就选择到了湖南,她带着小学毕业的弟弟加入到我们师大附中学生去靖县的行列,与我分到了一组。
直到下到生产队后,我才与她相识,这位北京来的女生,操着一口字正腔圆的京腔,非常好听,她有着北方人的那种率直,她身上常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似乎还留有点当初首都红卫兵的余威,接触后发觉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很快就与我们熟识了,也较快的适应了靖县的生活,迅速的与队上的社员打成了一片。
我们男生在背后都叫她“大大”,因为当地把姐姐叫做“大大”,入乡随俗,就唆使她弟弟喊她“大大”,久而久之我们也喊顺口了。69年4月,我们组八人一分为二,把我与另三人安排到舒家二队去了,她和弟弟等四人就留在了舒一队,69年9月招工时,她弟弟有幸被招走了。到了下放第三年,她组上只剩下她和另一女生了,我便加入到她们的伙食团来了(这我都在"失手"篇中有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我与她们和谐相处,不是因一件突发事件,打破了这种和谐,我的靖县生活也将不会留有遗憾的。
那是1971年11月下旬,我与往常一样到她们厨房吃中饭,走出拐角,还未踏进坪里,就看到一群社员围在厨房门口,她面红耳赤的在与一后生在争吵,那后生全家也在帮腔,我停顿了一下,以为他们还是在为写信的事在吵,这我就不方便介入了,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下,就掉头回屋里去了,这一掉头就留下了我永久的愧疚。我这人胆小怕事,最怕与社员吵架,见吵架就退避三舍,惹不起躲得起。所以一看见她在吵架我就离开,而不是上前去了解吵架的原因,我主观上的判断又是错误的,我事后才知道他们不是在为写信的事吵,而是另有原委。
这里我先把写信一事交代一下,这位北京知青很受队上社员的欢迎,她们队上一男青年,就是与她吵架那人,也是上过中学的,个子较高,肤色稍白,五官端正,在她们一队的社员中鹤立鸡群。他眼光较高,二十来岁还未婚,但他却看上了这位北京知青,竟给她写了封求爱信。当然此事不成,但这事却给传开了,队上的社员都笑话那青年,弄得那青年很没面子的,虽然事情已过去许多日子,他们之间却已结芥蒂。所以我一见她和那后生子吵架,便误认为他们仍在为那事在吵,便作出了回避。
等吵架结束后,我才去了她们那里,发现Z一脸悲怆,没等我开口,另一女生忙告诉我,她被打了,我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事情是从她们队上丢失肥皂而引起的,保管员发现放在仓库楼上的肥皂少了几块,这肥皂也就是靖县本地产的桐油肥皂,黑不溜湫的,商店里还买不到,还是计划配给生产队灭虫用的,这仓库的楼上又是队上的会议室,那些天晚上都要学习57号文件批林,肥皂不知什么时候被人偷去的?于是队长找她们,因为她们是住在仓库的楼下,她们的厨房门正对着仓库的楼梯口,进出仓库的人必须要经过厨房门口,所以,问她们看见有谁拿走肥皂?她听到肥皂被盗也很愤慨,出于对集体财产的爱护,就尽力回忆提供线索,说是看过那青年下楼时手中握着一块黑东西,不知是不是肥皂?这队长也简单,就直接找到那青年,并说出是她揭发的,那青年还在为写信的事而恼怒,现在又告他偷肥皂,便火冒三丈,冲到她们房里质问,还动手打了她两下,他父母也赶来帮腔。打人的场面我没看到,看到的已是在争吵阶段了,我竟以不是她们队上的人不便插手为理由而离开,实在太不应该了,不管怎么说,两个弱女子遭人围攻,作为一个组上的,是应该挺身而出。
她为被打一事而伤心不已,她抱怨我见死不救,她虽没多加指责,但从她的满含泪水的眼中,却分明能感觉到她对我的鄙视,我羞愧难言,无法为自己辩护,我至今还记得她那种带有责备的眼神。她俩还担心他们家再来打骂,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正想要以行动来补救我的过失,便提议与她们换房。她俩住的房子是在一队仓库楼下,独门独户,四周无人,不安全,我住在二队的房子,是团子里的中间地带,周围都是二队的人,隔壁有小H和房东,相对安全些,她们同意了,就这样我们当即互换了房间。
见我们互换房住,她们的队长找了我,说这是仓库,我不是这队上的人,出了事我要负责的。我正在为她被打一事气愤,破天荒地与他顶了起来,我负什么责?你们队上把打人的事处理好,我自然不住这里了,不处理好你们要负责,他没话说了。过了两天,队上仍无动静,社员对我们也冷漠了许多,我们也有些提心吊胆的。
第三天傍晚,那青年在我们厨房外耀武扬威的,这时从公社方向下来了一行人,那青年知道是来找他的,想上前为自己辩护,公社干部不容他分说,就一索子将他捆了押往公社,他父母听到消息急忙赶来,哭哭啼啼的跟在后面。原来是她看到队上不管,就告到公社去了,这我怎么又没想到,我们离公社这么近啊。当时,中央有文件要各地落实知识青年政策,公社对这桩事特重视,正好抓典型,所以就有了上面抓人的一幕。
公社又将这事报告给县里,县里也重视,成立了有公安和知青办组成的工作组,在公社的陪同下,直接到她们队上实地调查此案,连大队干部都不让来。工作组看了现场,听取了她们的控诉,又询问了队长和几个社员,没能做出盗窃的结论,但肯定打人是错的,队上不制止,不处理也是错误的。工作组来后,队上对我们客气多了,再不提要我负责仓库安全的事了。
又过了几天,工作组和公社作出决定,责成同乐大队在社员大会上批判打知青事件,以杜绝此事再次发生。批判会是在铺口中学礼堂里召开的,全大队的人都掺加了,那打人的青年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我也作为知青代表上台发言,我本是怯台的,在学校时连讲台都不敢上的,这次为了补救我的过失,我鼓起勇气站在台上,扯起喉咙大声指责那青年。散会后,知青们笑我在台上歇嘶底里的,我也知道自己有些失常,但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这次的会知青们还是满意的,至少给了当地人一个警示,不能再欺负知青了。
肥皂事件后,她俩与队上的关系有些疏远了,她俩都是在大队当民办教师,与队上的人接触少了,由于她们担心队上会为难她们,另一女生在第二年就转走了。我知道在这件事上她们对我有看法,我也不好老面对她那种责备的眼光,也想找机会对她解释清楚,让我能少一份自责,少一份内疚的,但一直鼓不起勇气来。之后,队上经常派到外面出工,先去金麦修水库,而后又上排牙山守野猪,秋收后到了公社基建队,大部分时间只她一人在组上,显得较寂寞的。1972年的年底,我被招工了,因招工的单位是派车来接我们的,走得突然,她正在上课,没来得及与她告别,但我已拜托我们二队,把我年终分红的钱和粮全留给了她,以弥补我心中的愧憾。
在往后的日子里,这事长期的困扰着我的心,我时时留意她的动向,到处打听她的消息,听到她终于回到了北京,在北医大(现北大医学部)搞党委工作,我很替高兴,终于回到北京了。2006年我在湖南知青网上写了对这事的回忆,想不到也被她看到了,今年的春节,她趁回长沙探望父母之际,专程到了我家冰释前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