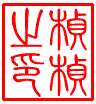挑堤
吃早饭时,我和易明没像以前一样有说有笑,而是显出一副丧气的模样。
“怎么了,今天又是多云转阴天,你们两个干脆还落点雨,撒几滴猫尿就会转晴的。”湘姐揶揄着说。
“真过不得想。” 我叹口气说:“许龙这样的人招工居然捷足先登,整天东游西荡的;还有我们大队那几个幸运儿,工分还没我们一半多,推荐时他们连名字都没人提,但就是有份!”
易明愤愤地说:“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龙书记说得几多好听,只要好好干,一定重点考虑。我们这些人都上当受骗了!”
“这社会不平之事还多着呢,你们不必自暴自弃,今后的日子还长,留得清山在,不怕没柴烧。”湘姐接着安慰道:“你们比比我们老知青,下乡五、六年,年纪都一把了,至今前途渺茫,不知出路在何方?好多人还在打单身。这些人想在乡下成个家吧,心又不甘,究竟一辈子的事啊!不成家吧,自然规律又难以违背,有的知青都快三十岁了。哎!这样的日子何日是尽头?”湘姐说着说着自己掉起了眼泪。
看到湘姐为了安慰我俩,反而将自己的眼泪安慰出来了,我连忙阴转多云道: “湘姐,你说得对,我们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今后是要想开点,少去想那些骗人的把戏!”
易明接着说:“确实,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如果按数学的推理法推理,那么希望越小,失望也就越小,不抱希望,也就没有失望了。”
我翘起大拇指:“到底是数学王子,还能活学活用,华罗庚怎么没把你收去当弟子呀!”
“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在这方面搞出点名堂的。”易明似乎忘记了这些天来的苦恼,开始说起有点志向的大话来。
湘姐此时笑了起来:“你们哪一天真的发达了,不会忘记我这个黄脸婆吧,到那时,我给你们当保姆还是可以的。”
三人顿时大笑起来。
“什么好事笑得这么开心啊?”队长走进来。
“队长,您好早啊!”我连忙打招呼。
“上面挑堤的任务下来了,刘东、易明你们两人都去,今天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队长接着又说:“这一去就是半个月,家里就靠湘姐打招呼了。”
易明急着到菜园收拾,湘姐也跟着去帮忙。易明向湘姐交代这园子的一切事项,什么韭菜割了一定要记得盖上草木灰;萝卜白菜不要蓄得太老;大白菜长到何时要记得用草捆起来,否则难卷心……
我将水缸挑满,又挑着一担谷去打米,然后拿起柴刀又到山上砍了一担满满的茅柴,后来还想起湘姐房门的门拴松动了,又拿着工具将其修好。
湘姐帮着我和易名清理好要带的用品,将两人开了口子的衣裤用针线缝好……
次日清早,湘姐搞熟早饭喊我俩吃了,又朝两人口袋里塞上几个盐茶鸡蛋,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中饭吃。
临走,湘姐一再叮嘱:挑堤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冷暖,在外要相互照顾。
跟着队伍走了好远,我回头一看,湘姐还站在门口目送。我想这多像当年抗日时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情景。我还联想:有谁找了湘姐这人做妻子,那真算有福气,自己今后找对象就要找湘姐这样的女人,会体贴关心人。
一行人步行三十多里,终于到达目的地。工地上满是人,其中还有不少知青。知青都愿意上堤,因堤上吃大锅饭,不要自己做!
挑堤就是将原来的旧堤加高加宽加固,打的是人海战术,众多的人挑的挑,挖的挖,整的整,一派繁忙景象。工地上的高音喇叭传出女播音员好听的标准普通话。
突然,只听得喇叭声嘎然而止。不久有一干部模样的人跑到工地喊:“有谁会修广播?”
工地上没人应。此时队长对着易明说:“还不快去露一手!”
易明走进广播室,那位女广播员原来是曾参观过自己菜园的长沙知青张云芳。
“啊,想不到是你,好甜的声音哇!”易明故作惊讶道。
“是你,种菜大王,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当后勤,修理修理呀。”
“看不出你还有这套本事,跟哪个学的?”
“自学成才吧。”易明说着就开始捣腾起来。不一会,喇叭又嘹亮地响了起来。
那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拍着易明的肩膀:“不错,妙手回春。”张云芳介绍说:“他叫易明,是河堤三队的知青,这位是我们工地的总指挥鲁队长。
易明握着鲁队长的手:“你好,鲁队长。”
“小易,你有这门子技术顶好,干脆就到广播室来负责维修和征稿。”
张云芳听鲁队长这么一说,高兴道:“那太好了,我们两人搭档。”易明说:“那要找我们队长商量,看他同意啵。”
“那有什么不同意,我这就给他说去。”鲁队长说着出了门。
不一会鲁队长进来了,对着易明说:“跟你们队长说好了,没意见,你就在这里好好干吧,以后还有机会用得上你的。”
“谢谢鲁队长。”易明接着说:“我现在是不是可以下去征稿了?”
“好吧,我先带你出去走一圈,让你熟悉一下。”易明跟着鲁队长沿着长长的水渠走去。
我和黄大伯一起挖土,边挖边问黄大伯:“这水渠是什么时候开的?”
“五八年呀!那时我们都参加了。”黄大伯沉默一会继续道:“想起当时开这水渠,现在还觉心寒。”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那时在这工地上干部不让你穿衣服,落雪天还要叫你打赤膊挑堤呢。”
“那又是为什么?”
“不穿衣会冷啊,一冷就会拼命干呀!”
“真这样?简直不可理喻!”我露出惊讶的神色。
“还有比这更厉害的,有的干部还打人,如果有谁不服调配或偷懒磨洋工,干部就拿皮带抽,你还不能喊痛。”
“有这样的干部?”我不敢相信。
“怎么没有!我们队上李为林就是这种人。他当时是大队队长,动辙就打人,好凶喔,人家叫他南霸天!”
我知道李为林,只是从未看见他出过工,有时只见他用手扶着脑袋,嘴里直哼哼。据说他是得了剧烈的头痛病,大小医院跑遍,只是诊不好。
“不知道这家伙这么凶!”我愤愤地说。
“他后来得了这不治之症,痛得喊爹叫娘,都没哪个同情他,他这是报应呢!”黄大伯说到这,脸上的青筋都暴露出来,显得异常激动。
我没再言语,身上的血在涌动,仿佛自己也回到了那个野蛮时代,看见那个李为林正在拿着皮带朝自己抽来。但自己却没像其他人奴隶般的默默忍受,而是夺过皮带狠狠地回敬那个暴徒,站在旁边的人欢呼起来。这时他们仿佛才明白,人也是可以反抗的。
太阳落山了,人们走进工棚伙房。工地食堂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各自负责。生产队大师傅李运量(李运田哥)拿起瓢分着菜。一大盆米饭加上萝卜白菜,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干着这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有什么东西不好吃呢?我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想。
易明则和那些工程部的人员一起吃饭,伙食比生产队的略好一点,有时菜里面还能看见片把肉。他吃过饭和张云芳来到工棚,邀我去知青处玩。
张云芳带着我俩沿堤走了好远,在一个工棚见到了李强。然后李强又带上他们找到其他知青,最后足有十几位相聚一起。
大家坐在一块空坪上,一起谈笑,唱歌。众人吆喝着李强和张云芳来一个对唱。坐在旁边的一位知青悄悄告诉我说,他俩现在是一对。
他俩唱了刘三姐的一首《世上只有藤缠树》。黑夜中虽不能看见他俩的眉目传情,听起来却是声情并茂,配合默契。情人唱情歌,当然能获得大家阵阵掌声。
张云芳客气地请易明来一曲。易明也没推辞,唱了一首《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刚一亮嗓,即倾倒众人,掌声即刻响起来。唱毕,张云芳惊叹:“想不到易明唱歌还是专业水平!”说对了,原来易明曾是长沙市红领巾歌舞团的。
易明此时介绍我的笛子吹得好,只可惜笛子没带在身边。有人听说后,连忙进工棚拿出一支c调笛。我接过来吹了支《牧民新歌》,在这寂静的夜晚,那清脆悦耳的笛音惹来众多老乡站在旁边欣赏。一曲刚毕,众人又吆喝着要再来一首。我一连吹了三首,再也不肯吹了。我知道,还有一些知青想借此一展歌喉。
果然,有人唱了首用《你送我一支玫瑰花》的曲调改编的知青歌。
我是一个知识青年,
我的生活没有来源,
上餐是萝卜丝,
下餐是萝卜片,
围着萝卜打转转。
……
歌声引起大家有些苦涩的笑声,笑声中,一位光头知青站起来向众人打一拱手:“各位别笑,我现在献歌一首,歌名是电影白毛女里的〈〈扎红头绳〉〉:
人家没钱买花戴,
我爹有钱不能买,
因为我是个光脑袋,
买来花儿没处戴。
哎嗨哎嗨呀,
没呀没处戴。
……
光头刚一落音,众人大笑,我和易明笑得前仰后俯,感觉好开心。
接下来有人要一位叫马力来一首。马力于是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并没急着唱,而是先来了段深情道白:“我要为大家演唱的是一首知青原创歌曲,这首歌的词曲都很优美,歌颂了知识青年的乡情、爱情、命运和理想。这首歌已经在全国各地的知青中广泛流传,深受知青喜爱。但不幸的是,歌的词曲作者因此而被立案查处。现在请大家听一听这支被查处的所谓禁歌: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
金色的扬子江畔,可爱的南京古城,
阿拉的家乡。
啊!
长虹般的大桥,
直冲云霄横跨长江,
巍巍钟山虎踞着阿拉的家乡。
告别了家乡,告别了爹娘,
挥手间天各一方。
可爱的亲人们啦,阿拉的姑娘。
啊!
我梦中的太阳,
照亮生命温暖心怀,
座座青山隔不断阿拉的姑娘。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
繁重地修补地球,是我们神圣的职责,这是阿拉的命运。
啊!
伸出我们的双手,拨开云雾迎来霞光,
总会有明天,
定会实现阿拉的理想。
动人的旋律,优美的歌词,加上马力深沉的演唱,使大家沉浸在激动而忧伤的意境之中。我深深地记住了这首歌,记住了唱歌的马力:高高的个子,结实粗壮,一副低沉浑厚而极富感染力的嗓音,且是正宗的男中音。
夜深沉,众知青依依惜别。
旭日东升,工地上又繁忙起来,高音喇叭放着现代京剧〈〈沙家浜〉〉片段。
我从低洼处一担担地往堤上挑着土,湿土好重,不一会身上直冒汗,脱得只剩下件衬衣。此时喇叭里响起了张云芳柔美的声音:战斗在工地上的广大社员、知青同志们,连日来,大家的干劲高,工程进度快,各生产队都是你追我赶,涌现出不少好人好事,如河堤大队第三生产队,在林队长的亲自带领下,挑堤进度走在了最前面,他们个个生龙活虎,尤其是该队知青刘东更是一马当先,肩上担子重,脚下步子快……
我听了自语:易明这小子真讨厌,又在搞“近水楼台先得月”,只要将生产队队长吹一吹就行了,何必要将我捧出来啰。
这时堤上远处走来一些人,林队长说可能是公社干部下来检查工作。走近一看,果真是公社龙书记带着一班人过来了。林队长连忙跟书记打了招呼。此时龙书记看见了我,立即说:“小刘,不错!上了广播,你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龙书记,您怕只是口里的啵,我和易明表现再好还不是无济于事,到底是重在表现还是重在出身?太不公平了吧!我们留在这里的还有什么想头?!”
龙书记此时竟有些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还是旁边的人打圆场:“龙书记还有其它重要事,以后再说吧。”说完扬长而去。
看着这些人的背影,我觉得即使这一辈子招工不上,也为刚才自己说的这番话感到痛快,值得。
晚上,将白天跟龙书记说的这番话告诉了易明。易明激动道:“说得好,你不仅说出了心里话,而且代表了很多敢怒而不敢言的人的心声。”
工地仍像往日一样呈现出繁忙景象,我挥汗如雨挑着担子,脑子里此时什么也不想,只想着早点收工吃饭。挑堤以来,最难受的是肚子饿,工地上饭菜没油水,劳动强度大,吃得再多也撑不到收工。此时有人问队长何时能打打牙祭。队长回答过几天快完工时会考虑,大家都在盼着那个好日子的到来。
好日子终于来了,晚饭时,队长安排李运量烧了一大锅红烧肉,还要我去广播站将易明叫来,易明把张云芳也一起请来了。
开餐时,生产队的弟兄们个个如饿狼扑食。队长还在一边加油打气:“大家只管吃,我们今天要吃一个痛快!”
菜碗里的肉风卷残云般刚吃完,李运量又用大菜瓢上满,还说什么今天猛过共产主义,机会难得。此时的我毫不示弱,一口一块肉,还尽拣块子大的。
大师傅李运量学了他母亲的烹调技术,弄出来的红烧肉肥而不腻,着实逗人胃口。此时大家像在比赛,看谁吃得多。
机会难得,吃少了划不来,多吃点,放肆吃,吃得肚皮发胀才过得想,才不会后悔,这是大家的想法,当然也包括我。
夜晚,不少人摸着肚皮只哼哼,粪缸的生意好得不行,有的等不急,即随地大便起来,此时绝对没人怪罪。我捧着肚子往山上不知跑了多少回。
第二天开工,大家拖拉着脚步在堤上干活,反没了往日那股子劲。
总算完成了任务,队长带着大家打道回府。一路上,笑谈起吃肉之事,队长后悔不迭道:“不知一次弄那么多肉做什么?大家像牢里死刑犯一样,吃了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