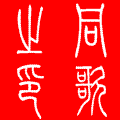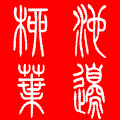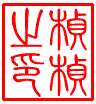又是清明扫墓的时节,我又一次来到黄海的坟头。
她长眠于地下已经6个年头了;我没有忘记她生前给我念起的那两句诗 :“千遍叮咛万回嘱,莫教孤冢草萧萧”。每来一次,我都要细细地清洁墓地,摆上祭品,喃喃自语,和她进行心灵的沟通;不管人去后有不有在天之灵,我都相信她能听见。
流经安乡的那条河叫淞濨,流经德山底下的那条河叫沅水,它们都奔向洞庭湖。这两条河承载着我们的相知相恋与年轻时代的悲欢离合。虢家洲是那时我们回故乡长沙最近的船码头,它位于淞濨河西岸;74年她顶职回长,我从这里送她到茅草街,后来又多次在这里把她迎来送往。位于德山山麓的七一厂是我工厂生涯的第一站,76年初夏,她背个军挎包跟父亲说“我到常德结婚去!”就登上了去做新娘的客船。到79年我调回长沙,夫妻才得以相聚。期间从我们的初恋到热恋到结婚,再到女儿出世长到一岁多,整整五年的时间,辗转于洞庭湖野,靠两地书交流情感和沟通信息。后来黄海把我们五年的来往书信整理得清清彻彻,说是到老时再拿出来细看;而今,那一大本信稿还静静地躺在我的箱角,而人已了无痕。哎!辛苦共尝偏早去,头白鸳鸯失伴飞;暮雨朝云皆往事,只有涛声似旧时了。
后来的二十多年,我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一边努力工作,一边悉心培育女儿,度过了多少快乐、温馨的时光。不料90年代中期开始,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终于在女儿高考的那一年染上恶疾;在与病魔抗争6年之后,在女儿读研二的时候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
在病中我曾鼓励她顽强生活,一定要看到我们的女儿长大成人。我曾经跟她讲,第一步要看到女儿上大学;第二步要看到女儿参加工作;再进一步争取看到女儿成家生子;如果这些都能看到,也不枉你一辈子的辛劳,死亦能瞑目;她也是抱着这种信念与病魔抗争的。不料自然规律忒无情,倏地天人阻隔!
我一辈子最遗憾的事是没能救活黄海。于今站在她的坟头,有一种绵绵不绝的遗恨!
黄海呀,如何三十年来事,只抵春宵一梦长?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