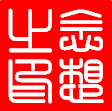队上的仓库,由于距社员聚居的弯里还有一小段路,且在孤零零的山坡上,秋收后,为防止谷物被盗,要安排人每晚看守。起先还大家轮着去,后来我们知青了解到住在仓库点灯用的是队上的油,晚上可以放心大胆地看书, 守仓库便成了知青的专利。
看到我们守仓库尽心尽力,队上又推举我在俞氏之后当了一段仓库保管员。这时正是双抢过后,仓库堆满了刚收割下来的新谷子,保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将谷子从库房内担出来,摊在仓库前三合土砸就的晒谷坪上,过一段时间用木制的耙子翻一遍。太阳落山后又重新担回库房去。谷子担进担出还有社员帮着一起挑,翻晒谷子那就是保管员一人的事了。整个白天,除了隔一段时间翻一遍谷子以外,再没有其它事可干,而人又不能离开,只好坐在楼梯上看收集来的小说。有时看得入迷,连社员家的鸡一群群偷跑上来吃谷子都觉察不出,为此还挨过队长的呵斥。又要看书,还要时不时赶鸡,搞得人心里烦燥。一时心血来潮,竟将放在仓库角落里的1605农药倒了点出来,拌上一些谷子,洒在鸡们经过的道上。心想开会时队长已宣布晒谷期间不准将鸡放出来,而个别人为自家的鸡也能分享丰收的果实,以为知青好欺负,早饭后就偷偷将鸡赶出来,跑到晒谷坪撒欢。这样搞了几次,实在看不下去,才想出这么个主意,让你们知道知青也不是那么好惹的。谁知此举马上见效,中午收工后就有社员提着死鸡到陶组长家告状了。慌得陶组长饭都来不及吃,跑上仓库问缘由,待我将前后情况讲清后,他也不好说什么,何况已造成了既成事实,只得叮嘱我不管谁来吵或闹,都不要和他们顶撞,一切由他来处置。这样整个下午连吃晚饭时,我都没敢回宿舍,只听弯里时不时传来女人的骂街声。那天仓库周围毒死的鸡少说也有十几只,此事过去几天,心里还有点后怕。好在毒死的是畜牲,要是不小心毒死了人,那我此后的人生是个什么样子,真还不好说。有些事情,的确是一念之差,结果却大相庭径。这样的例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层出不穷,这里还真勾起了我少年时的一段回忆——
那是五七年暑期,我还在路边井小学读二年级,正是懵懵懂懂的年纪。我家住在一所大杂院内,院后隔一堵墙就是铜铺街小学(我们也喊它江西小学),每天只听得高墙内传出断续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的声浪扰得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也不知所措,不知道学校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开学后,教我们数学的曹姓女教师突然离开了讲台,天天在学校拖起垃圾来。原来那么年轻漂亮,和蔼可亲的老师,一下子像老去了十岁。看她每天艰难地拖着垃圾车往返于学校与相隔十几里路的湘江边粪码头的垃圾埸,我们都于心不忍。天天放学后自发地帮她推板车。而我们的班主任——也是一位女教师却屡屡叫我们不要可怜她,说她是右派份子,是反党的(我们的女班主任老师就是因为反右有功而入党的)。以我们那时的理解能力,是没法将右派份子——反党——不能帮助她这些事物联系到一起来的,凭直觉,平时我们觉得她比班主任要可亲些。她的与我们一般大、长得像个瓷娃娃似的女儿就在我们班上,我们没有理由不与她母女往来。一边是深恶痛绝的“右派”;一边是又像大姐姐又像妈妈的老师,我心理上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一个事物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感受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而那时,这种事谁能解释得清呢?
所以后来看到队上也有一个曾经是小学教员的女右派时,我头脑中立刻浮现出十年前所见过的场景,不由得对这个“右派”有所同情起来。特别是她那两个小不点的女儿,以现在的标准,只能算是小学生,却整天与我们泥里水里在一块流汗。小小年纪,却要担起与其身体不相称的生活的重担。我不知道当时她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我相信,在她们一生中,她们父母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以至祸及她们自身这道阴影,会始终保留在她们的记忆深处。
而等等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往往都被冠冕堂皇的理由所笼罩而变得义正词严,反右是这样,文革更是这样。早在文革之前的几年里,阶级斗争就已把人们搞得人心惶惶,再加上贯彻阶级路线的政策一出,硬性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朋友结仇、夫妻反目的悲剧在中国大地上便层出不穷。家庭有所谓历史问题的高分考生不是进共大就是下农村,便是我们那一辈学子的必然结局,理由当然还是贯彻阶级路线,可笑我当时还自作多情地想到学校去查分数,事后想来,真是幼稚得可以。
当时聊以自慰的是,文革后期,不管什么出身的人,统统下放到了农村,变成了靠工分吃饭的农民。然而此“农民”比起彼农民来,差距又何止十万八千里。到底由谁来同化谁,这是我至今未能搞懂的问题。接受“再教育”的成果,便是此后知青想方设法以招工、上学、当兵、病退为手段而逃离农村。后来从俞氏口中我还得知,早在武斗正酣时,也就是一部份知青杀回靖县参与武斗期间,他,以及一部份知青却从另外的途径开始了一次匪夷所思的大迁徙——目的也还是想脱离农村。
他们那次到安置办去要车票,与我们回靖县要路费的经历,颇有点相似。也许是安置办的人太麻木,也许是一心只想把知青打发走了事,当知青麻着胆子报出返乡的目的地为盐池时,他们竟然连盐池在哪个省都没搞清,立马就签发。于是俞氏他们非常顺利地领到离盐池最近的一个站的火车票。其实知青们心里明白,他们要去的目的地是新疆,盐池不过是从地图上随便选取的一个地名,想不到这个瞒天过海的计谋竟然骗过了安置办。
经过近一星期的枯燥而疲乏的旅行,他们终于到达新疆,一行人下车看到西北那荒凉的景象,与他们想象中的“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情景,相差十万八千里。一个个顿时傻了眼,同行的女知青更是惊慌得不知所措。但来都来了,吃后悔药已晚,只好硬着头皮往前闯。因为那时在知青中一直流传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全国大量招收知识青年,不要户口,不要毕业证,只要能够过去,马上就发军装,享受供给制的传言。在靖县是“修地球”,到新疆了不得还是“修地球”,但能够成为兵团战士,由拿工分变成拿工资,不比当知青好过一百倍吗?马克思早就说过:无产者在斗争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反正已经到了社会最底层,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舍弃了,何不趁此机会搏它一搏呢?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群知青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找新生活的道路。
可惜事与愿违,当他们找到一处生产建设兵团说明来意时,竟遭到对方的严词拒绝,并出示了中央关于遣返自行进疆的知青的文件。一路上的风餐露宿,一路上的不屈不挠,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真是出发时任何人都始料不及的。再找其他的单位,得到的是同前面一样的答复。眼看盘缠已尽,投靠无门,不得已,一干马只好又原路返回。本来雄心勃勃的一次远征,却杀翊而归。俞氏他们回来后,提起此事,愤激之情不时溢于言表。知青在那时急于寻求出路的彷徨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下乡已近四年,家乡在我们的记忆中已渐渐变得模糊。手上的老茧,脚底的硬皮,使得我们与当地社员在外表上已没有多大区别。几年来,农村清苦的物质生活和相对贫乏的精神生活,将我们这群城市下来的青年打磨得近乎野蛮、自暴和无所适从。正常的情感被扭曲,感情生活一片空白。尽管我们不想因循着当地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生活轨迹走下去,但另外的道路在那里呢?要说像前沙俄十月党人流放西北利亚吧,我们又没有他们那样远大的志向;要说像历代的屯垦戌边吧,我们又没他们那样严密的组织。再说最近一年来下放的知青,那都是在文革中立下过赫赫战功的红卫兵小将呀,一旦不需要他们的力量了,就像换季时脱掉的旧棉袄一样,被随手扔掉了,扔到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成了一群被主流社会所遗忘的前世孑民。好在中国的农村是如此的广袤,中国的农民是如此的善良,他们毫无抵触的接纳了被伟大领袖一声号令而招唤下来的千百万城市青年学生。但下来后他们的道路怎么走?他们今后的出路在哪里?伟大领袖这时已无暇顾及,贫下中农也没有这个义务。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知青,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道路将指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