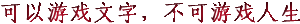从那心房流出来的……
孩提时起,我就为了;“人的情感是受大脑的支配还是受心脏的支配”这样的问题反复的问自己。尽管后来老师告诉我;“人的感情是受大脑神经支配的……”但似乎到现在这个问题我还是没有完全搞清楚,我对它的疑惑是;“如果说情感是受大脑神经支配的话,为什么人们每当受到外界的刺激时,心脏的反应往往大于大脑”那种感觉是一股异样的、带有一丝辛酸感觉的东西颤抖着从心房涌向全身、从眼睛夺眶而出而不由自主的。
当然,这种情况不是常有的。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吧。可是最近却有被它牵动着了好几次。
今年(三月十七日)我们下乡到浏阳的知青们一齐相约“浏阳之春”。从网上看到通知起,我就对组织这样一个活动抱有一种期望值不高的心态。这几十百号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和单位,有的还不认识,虽说有一个、天下知青是一家的信念为出发点。但是一路上、吃、看、玩,走、行、住和安全防范都是一个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出乎我的意料,这次活动搞得很成功。下午聚在一起茶欢的时候,大家唱啊、跳啊的拿出节目渲泄自己的情感。我认为大伙表演的东西,精湛、情感丰富。是一种生活艺术的积累,是知青人文化素养的体现。他们的专业甚至于一些艺术团体都不能比拟。听说他们当中有一些是“知青艺术团的成员”。“知青艺术团”这个带有浓厚的知识青年色彩的团体,十几年来,一如既往坚持为社会服务,为“三农”服务。受到各界的肯定和农民朋友的好评。他们是知青人中的优秀群体,是让社会从另一角度审视“知青人”的窗口。它使农民朋友对知青人过去的一些消极的看法得到极大的改善。九四年的一次下乡演出后,我询问一个当地的农村基层干部对演出的看法,他感叹地对我说;“这是我们本地方有史以来最认真的、最令人感动的、最受欢迎的、最好看的节目(他这里说的“节目”我理解为“文化艺术”)。他一连用了四个“最”字,这使我的印象极深。现在想到那些,又看到他们在这里激情认真的表演,它使人一阵不由自主的感动,那一种异样的、带有一丝丝辛酸味儿的、从心房涌出的东西,它突破了眼眶的防守……
当天晚上我没回长沙,被朋友留在家里。次日,一些昨天没来得及见面的朋友们又在一起小聚。席间,我们几个老知青相互的戏谑对方老了。是的我们都老了,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还会继续老。从过去那热血沸腾的小青年到眼前的老头子,岁月年轮毫不掩饰地雕刻在我们的脸上。
张君,我们中的一个,他是先我一年下到大围山的。下乡的十几年中,犁田耙滚、浸种育秧农活是自不必说,还兼生产队会计多年。十几年知青生活的辛酸苦辣,他走 了过来。娶了当地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生了几个孩子。77年安排到当地的企业。他和所有的调上来的知青一样,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他(她)们更加加倍努力的工作。他(她)们想到要相信单位组织,想到要努力回报社会,想到要对得起做一个领导阶级的一员“工人”的荣誉,想到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他(她)们唯独没有想到还会有下岗、破产、失业。几十年国家集体主义的文化教育,教给了他(她)们很多。唯独没有教他(她)们
如何的应对眼前的一切。社会转型的挡口上,他们楞住了,就在他们楞住的时候,一部分人已经从这个起跑点跑出了好几圈了。其后的结果是生涩的,老婆多病,孩子们无稳定收入,自己所在单位又改革破产,又恰巧不到退休的年龄。这一来连“为斗米而折腰”的机会都没有了。席上有人说;现在不是有“低保”吗?是有,据偿试的人说,那是极不俱尊严的办法,那其中的几个“几要几不能有”类似于过去一段时期“几要几不准”。因此他们宁愿拖着孱弱的身体,用自己仅有的劳力为商品去换取日前的生活所需。“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之不屑也”。
张君举起自己的酒杯,巍巍峨峨的颤抖着(估计是老人常见的;帕金森氏病)和我们碰杯,等到撒撒落落地送到自己嘴边时,那杯中的小酒已所剩无几。他一仰头倒进口中,溢出的酒和水顺着那满是雏纹的嘴角流到他那因吞咽牵动的喉结边时,我望着那酒和水流着,眼前幻影出当年生龙活虎的战友的形影……其实我自己又何偿不是这样,还有许许多多当年的知青朋友又何偿不是一样呢?想到这,不禁又一股异样的、带着一丝丝辛酸味儿的、从心房里涌出的东西,它突破了我的眼眶。“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近十几年来,我快乐着、我痛苦着,我快乐人们的快乐,我痛苦人们的痛苦,这其中唯独没我自己,因我知道,我只是一个“知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