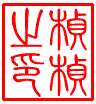双抢啊,双抢!
下乡后,迎来第一个稻子黄了的季节,田里稻穗低垂,仿佛在向人们点头示意:成熟了,该收割了。
易明被安排在田里拖格子和做其它杂事,我少不了干田里的主要农活。
我和回乡知青秋山将田里打稻机踩得轰轰响。女人们把稻子割倒,男人们捧起来送到打稻机上,用双手掐着大把的稻穗,在带齿的滚轮上摁着滚几个来回,稻子就象被人剃了头一样成了光秃秃的草把。
刚开始觉得还有点新鲜,两只脚轮流用力踩着踏板,滚轮转得飞快,打稻机仿佛装上了一台功力强大的发动机。拖动打稻机时,我一声吼,机子被拖出老远。秋山提醒我:“日子长着呢,留点力气吧。”我没在意,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腿开始发酥,再后来,象灌了铅。
秋山讥笑道:“怎么,胯挡里那只马达短路了?”
“没事,正常着呢。”我如死了的鸭子——嘴硬。
烈日毫不留情地灸烤着大地,灸烤着田里的农人。稻田里的水已经晒得发烫,两腿烫得发痛。我一身泥,一身汗,像从水塘里捞出来似的。上烤下蒸,田里干活的个个成了“熟人”。
我边踩边思忖:要是能给这机子装上一只真正的马达该多好。人再有力气,也经不起这长时间的折腾啊!
夕阳西下,踩了一天打稻机,身子像散了架,进屋和衣倒在床上,晚饭也不想了。
第二天的任务是挑谷,一担湿谷至少一百六七十斤,而晒谷坪恰恰建在高处。从底处往高处挑,挑得两腿直打颤。每次倒掉湿谷,挑着空担往回走时,一身才得以解放,被重担压呆了的脑子又活跃起来。
此时不由想起长沙西湖桥的沙子码头,船上的沙子被转扬带轻松地运到岸边,那堆起的沙堆就像一座座小山,倘若这挑谷的坡道上安装一条转扬带该多美!
唉!这地方电都没有,安装了有屁用?
烈日当头,风儿都不知躲哪去了,只有树上的知了在一个劲地鸣叫,此时真想变成齐天大圣,吹口气,呼来一片厚厚的云,跟在太阳底下,将太阳遮得严严实实;再唤来一阵风,将地上的热气身上的汗气统统赶跑,多惬意!
终于又送走疲乏不堪的一天。吃完晚饭,坐在禾场休息。此时明月高挂,远处稀疏的星星在眨眼;屋前沟渠流水潺潺,四处蛙声一片,让人感觉这世界就是青蛙的了。
多美的夏夜啊!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我对易明说:“这样的月夜,城里的人们早该将竹床搬到外面乘凉了。孩子们一定躺在竹床上仰望星空,指画着北斗七星的方位,冥想着月宫里的嫦娥。”
易明说:“是呀!像这样的夜晚,小时候躺在竹床上总能看到头上的两片云,但发觉两片云从没有走到一起过,总像隔着一条湘江。觉得奇怪,有一天指着天上两片云问爸,为什么其它的云都在走,而这两片云每天呆在这不动。我爸仰天一看,立即笑了起来。他告诉我说这不是云,是银河。这银河是由无数亿个地球一样的星球组成,因为离地球太远,不了解它的人还以为是两片云。我爸还告诉我,牛郎星和织女星就是在银河的两边。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天上的星座产生了极大兴趣,自从读书以来,我就一直在看有关天体的书籍,我现在能熟悉地指出好多个星座来。”
正想请易明告诉我一些星座位置时,突然响起了尖锐刺耳的哨声。
“喂!今天晚上有月亮,大家都到秧田扯秧去。”生产队长大声吆喝着。
白天,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烫脚,连蚂蝗也懒得出来觅食。可到了晚上,蚂蝗听到了水响,知道有美食送上门来了。
突然,觉得腿上一阵奇痒,抬腿一看,一条大蚂蝗已经胀得一身滚圆,叮在腿上一动不动。月光下的蚂蝗显得特别阴森,圆圆的,冷冷的。于是一巴掌将吸血鬼拍打下来,掐死!摸块石头将它砸得稀烂。这时腿上的鲜血还直流,止不住,学着老乡的经验用一根稻草缠住伤口,算是作个了结。
秧田里只有哗哗的扯秧水声,也许大家都太累了,懒得说话。此时想起下乡前在长沙听到的一个关于蚂蝗的故事,讲给易明和旁边的老乡们听。
我说有一次,长沙有所中学组织初中新生去农村劳动,出发前,老师叮嘱同学,田里有蚂蝗不要怕,万一被叮上,千万不能用手去扯,扯断就不好办了,叮在腿上的那一节就不得出来。同学们害怕地问,那该怎么办?老师说,你们必须记住,被蚂蝗叮了后,狠狠拍一巴掌就是,蚂蝗就会乖乖地掉下来。同学们将这一招牢牢地记在了心上。大家步行数十里,来到乡下稻田里插秧。突然,一女同学发现自己的腿被蚂蝗叮上了,顿时吓得哇哇叫,同学们见状连忙喊,快!给一巴掌。这女同学对着自己的右脸就是一巴掌。同学们提醒她打错地方了,她又毫不犹豫地打了左脸一巴掌。
秧田里的人听完故事,个个笑得前仰后俯,疲劳也被赶走些许。
此时四周的蛙声叫得更欢,它们白天不知躲在哪里歇凉,而到夜晚才出来觅食求偶。
扯秧的人们洗脚上岸。我和易明拖着疲乏的身子并肩而行。易明问:“人不知到底是否有来世?”
“我想有吧。”
“那我下世不想再变人了。”
“想变什么?”
“变个青蛙都比人强,比人还要快乐。”他又问我:“你想变什么?”
“我想变一只鸟,在蓝天白云中自由飞翔,比青蛙更快乐。”
“你比我想得还美啊!”
……
两人说着话到家了,摸黑进屋,没有洗澡换衣,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但谁也没心思去弄什么夜宵了,连洗澡换衣这样的重要环节都一概省掉,和衣倒在床上,眨眼就天亮了。
清早,出早工的哨音就象潘多拉魔盒发出的声音,让人听了发怵。我和易明翻身而起,眼睛还未睁开,踉踉跄跄向外走去……
后来,两小腿生出不少红点,奇痒,忍不住用手挠,挠破了直流黄水,接着开始发烂。我问秋山是何原因,他说是稻田皮炎,是因为两腿在田里长时间浸泡,移动,加之气温高,田里毒气重引起的。他还立即回家拿了药要我晚上洗了脚抹上。
洗脚后边抹边想:怎么全生产队就自己一人得稻田皮炎?第二天问秋山。秋山说:“俺这里人土生土长的,哪像你这样细皮嫩肉。”
不久,双腿的烂处开始向纵深发展。找到大队赤脚医生,方知患了此病抹药后不能下水田。难怪抹了药不见效!我想请假,但转而一想,在这关键时刻,谁会由于这点毛病猫在家里呢?于是继续忍着疼痛在田里冲锋陷阵,结果让两条腿吃了大亏。
一日收工后,洗脚时发现自己的腿已烂得更深了,仔细一瞧,能隐隐看见烂肉内的白骨。这时才有些恐惧起来。
找到队长:“队长,你看,我腿烂成这样,实在不行了。”队长看了下,显出为难的神色道:“小刘,队上劳力紧,你又是主劳力,立秋只有两天了,耽误不得啊!你是不是还坚持最后两天?”
我无言以对,在这关键时刻不想让队长为难,跛着腿又走向水田……。
双抢啊,双抢!总总一个月,像做了场恶梦,最后在生产队的磅秤上称了一下体重:还剩下一百零八斤,身上十几斤肉不知掉哪去了!
双抢完毕,队长表扬我,说我腿烂得稀烂还坚持干到底。
后来队长安排我晒谷,一段时间没下水,烂得见骨头的一双小腿,才慢慢长上了新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