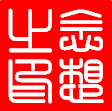下乡前,在家里也短距离挑过少量的自来水,比起乡下挑担子,那是不足一谈的。
下乡后,挑担子是必过的劳动大关。从不会挑担,到轻轻松松挑百多斤重的担子,这非得有一个历炼的过程。
初到队上,我们对农活,基本上什么也不懂,也不会。但没有任何条件可讲,更没有试用期。从一开始,就必须什么都得面对,什么都得去做,要靠挣工分养活自己了。第一次出工,所做的农活,就是远距离挑担子。
刚到乡下时,是春耕前季节。生产队在每年春插前,得将农田都撒上石灰,预防以及杀灭些病虫害,还能中和土质。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石灰窑,我队的石灰窑在马路对面八队靠大路边的小山丘上,距公社场上不到两里地,那里有可就地开采供烧石灰的岩石。烧石灰得用燃料——煤,而燃煤必须去到十几里路远的溪口大队煤矿挑回。
第一次挑着担子走远路的窘样还记忆犹新。我们几个知青用新扁担挑着新粪筐(筐:当地读qiang音,粪筐,就是长沙讲的“箢萁”,但结实得多,是农活中的重要工具。粪筐有系,不是一般的铁矮丝系,是用竹子扭成的硬撑直立的高系。高系的顶端部再缠扭点绳索成一个圆圈,以利放扁担,挑担歇担时就不必弯腰弓背),随着队上的男女老少社员踏上了挑煤之路。去溪口大队煤矿要经过公社场上,再过塘头大队地盘,顺小路往艮山口方向走。
一路上,开始还兴高采烈,但新扁担新粪筐压在肩上,对于还不会挑担的我们,也逐渐感觉这点份量的压力,十几里乡间路,越走越累,个个都累得气喘吁吁。挑煤要按煤到石灰窑后的重量多少记工分,社员们都赶着多跑几趟,多挑几担。大部队不会等着我们知青,早早甩开了我们只奔煤矿了。我们还只走了一小半路程,挑了煤回走的村民就已有不少。
我们终于到了溪口的煤矿所在地——小山中很原始很简陋的一个小煤窑。来不及喘气休息,便匆匆忙忙往各自粪筐里装煤,过秤。挑多的肯定是挑不动,来了又不能不挑,我装了四十多斤、也有装五六十斤的。返回的路上洋相百出,挑担的样子真难看。知青几人耸着肩、缩着头、弓着背,挑起了社员认为是很轻的担子,走上了回程。一路上,我们挑担的样子,逗得社员、路人直发笑,直议论。笑声、议论、指指点点让我们好难堪,更使我们感到“重”压下的几多难受。
挑着几十斤煤,一路上走不了几步就得歇气。初挑担,又不会换肩,只能硬挺着一个肩膀挑。那担子越挑越沉,肩膀越压越痛,脚越走越软......特别是走上下坡路,双脚直打跪,真的是走两步就得歇一下。走走歇歇,又累又饿,直觉得路老是走不完,太难以到岸了。不得已,一路上只有不断的将粪筐里的煤移到社员的筐里,以减轻重量。终于坚持到了石灰窑,煤再过秤,我的煤连带筐只剩三十多斤了。
那天,我们就只挑了一趟,挑回了那么点点煤。回到家,个个都只喊痛、累......
面对艰辛,我们没有逃避。我们经受了摔打锻炼,在努力学做各种农活中成长成熟了。挑担及其它许许多多农活,都没能再难倒我们。以后,我们挑担姿势的潇洒、优美,步伐的轻盈,也不亚于社员了。
多年后,回长沙探亲,住在五中的婆婆家。有几次遇上停自来水,我又重新挑起了担子,到马路对过的枫树山小学挑水。我挑着满满两桶水,不盈不洒,毫不费力,步履轻盈地行走在大马路上,时而还轻松的换换肩,那优美的挑担姿势也招来了不少路人、邻人的笑脸与一连串赞许。那个时刻,心里好美好自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