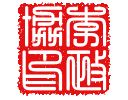蛇 的 趣 话
人怕蛇是普遍规律,据科学家研究,是从灵长类老祖先遗传下来的基因。我幼年也是如此,谈蛇色变,怕得要死。最早的记忆是,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听保姆爱爱讲岳麓山蟒蛇精的故事。说的是:古时候,岳麓山上的蟒蛇修炼成了精,想要吃人。摇身一变,变个道士来到城内,到处蛊惑人心,说是某月某日晚上,湘江上会出现一座天桥,那头有两盏灯笼照耀。抢先上桥过得河的就可以成仙。惹得许多人相信。届时,蟒蛇精现出原形,吐出长长的舌头搭成天桥,两只眼睛便成了灯笼。抢先过桥的人直接入了蛇腹。长沙太守叫陶侃的一眼识破诡计,张弓搭箭射去,“嗖嗖”两箭先射瞎了蛇精的双眼。然后,仗剑上前,一挥两断,斩了妖精,为民除害。听得我一身冰凉,气都不敢出,钻进爱爱的怀里,半天不敢出来,一个晚上都不许吹灯。好多年都不敢上岳麓山,更不敢去蟒蛇洞,连鳝鱼都不敢吃。及至年长,知青下乡,在农村见得蛇多了,胆子方才慢慢大了起来。
在湘西山区,蛇是极常见之物,即使坐在家中,有时也会从房梁上滚落下两条纠缠在一起的蛇,后来才知道,那是蛇在求偶。夏秋之季,凉爽的早晨,山区经常能看到一种独特的风景:在草棵子或灌木丛上会挂着一条条蛇蜕下的皮,卖到药铺里做得药。据说蛇的一生要蜕好几次皮,蛇长大了,老蛇皮就像过紧的衣服箍得难受。蛇便在岩石或砂土上磨嘴巴,直到将老蛇皮磨开一个口子。找一株够结实的草棵或灌木杈,将老蛇皮挂住,蛇头努力往外挣,出得一半,“哧溜”一声就全蜕下了。蛇迅速游走,只留下蛇皮筒筒挂在那里随风飘动,像清明节放的蝌蚪风筝,也像随地丢弃的那种极薄透明的塑料袋子。
湘西蛇多,蛇吃老鼠、偷蛋都不稀奇,最精彩的要数蛇与“板板”斗架。有一次放工回来,在村头小溪边洗手脚,我亲眼目睹了那精彩的一幕。“板板”是生活水边岩板上一种体形巨大的黑蛤蟆,学名好象叫岩蛙,水蛇悄悄窜上去缠上了它。“板板”先是不急不忙,一动不动,只拼命地鼓气,把自己的肚子鼓成了个圆圆的气球。水蛇想囫囵吞,吞不下;想咬,“板板”的皮又硬,咬不进;想把“板板”缠死,一不留神,“板板”机智地放光了气,身子魔术般地变得苗条,“嗉”地一下从蛇的缠绕中滑跳出来,反掐住了水蛇的颈子不放手。几番下来,水蛇没了力气,只好悄悄溜走。“板板”于是又跳到岩板上,“蝈蝈”地唱起歌来,仿佛打了胜仗的大将军在骄傲地公开宣布。打个平手是经常的,但据说也有“板板”最后把水蛇当了点心的,不过我没有亲眼所见就是。
我有一次被蛇吓得魂飞魄散。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从大队部摸夜路回来,背篓里背着几十斤磷肥。没有带手电,不好意思,其实手电是有的,只是没钱买电池,早已打不亮了。从大队书记家里取了一把黄篾(竹子取青篾后剩下的篾片),点起火把就上路了,一路哼着歌给自己壮胆。刚过岭脊,一阵山风,吹灭了篾片火把。赶紧蹲下身来吹,哪里还吹得燃。只得摇动着那把余烬,借助依稀的红光看脚下的小路,心里默念着"晴天看白不看黑,雨天看黑不看白"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步一个脚印。阿弥陀佛,直走到住的屋场前,平安无事。背着重负走上熟悉的坪场,突然第六感觉有点不对劲。即将踏下的脚下,黑糊糊的一团是什么?用几乎燃尽的火把一照,汗毛立时倒竖。不好!卷曲成一团的是条五步蛇,当地俗称“烂草鞋”的。此蛇极毒,咬人五步之内必倒,而且无药可救。五步蛇又极懒,多半时间蜷缩睡觉,但你要惹恼了它,报复起来没商量。思维如电光石火般迅疾,一个成语“狗急跳墙”在脑海里跳将出来,情况紧急,也顾不得修饰斟酌,用在自己身上恰不恰当。我猛地将即将踏下的右脚收回来,同时左脚发力,纵身一跃,喘息间已是连人带篓到了六七尺开外、两尺多高的台基之上!孪心跳到了口里,自己拍打着胸口后怕:崽啊崽,刚才这脚要是踩下去,明天就不需要早饭米了,缸里还有七八斤米不是便宜了别个?!现在回想起来,又有了新的见解:哪个运动员要是有我当年那股子爆发力,参加个什么负重立地跳远,只怕随便子都要打破项把两项奥运会纪录!
不过也有人和蛇都互相害怕的时候。那是七○年荞麦开花的季节,县里安置办抽调我去参加调查全县下放人员的情况。每人分一个片,任务紧,一家一家,连赶地赶地挨家走访。那日从一家告辞出来,已是红日西沉,主人好心留宿,我谢绝了。翻过前面这道岭就到了下一家,自信凭我的脚力,天黑前到达不成问题。快步如飞,一线石板路上得岭来,仿佛武松上了景阳岗,又进了野猪林。夜虫在叫唤,归鸟在啾鸣,角麂子声声凄厉呼唤同伴,晚风四起,直教人身上一阵阵发紧。过了黑压压的林子,路就分了叉。右边一条宽石板路,左边一条窄毛毛路,并无指路碑。估摸一下,乡有乡道,村有村路,去另一个乡,自然拣好路走。“下坡如扫地”,走得风快,下了两三里,却越走越不对:路越走越窄,最后竟然没了路,山谷里躺着一片荞麦地。还不死心,从荞麦棵子里深一脚浅一脚穿过,就到了一条小河边,路断了。往下游看,远远看得见我要去的村落沉浸在暮蔼之中,但两岸悬崖峭壁,无法攀缘。死了这条心,当下转身,走回头路。糟糕!一条黑忽忽的“乌梢公”挡住了我。这厮碗口粗细,抬起前半截身子,和我一般高,怕莫有几十百把斤,它吐着长长的信子,口里还发出“咝咝”的声音,身子微微地前后左右摆动。我想退避,身后就是湍急的小河,两边都是峭壁。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我绝对不是它的对手,这回只怕是要被它“荞麦田里捉乌龟”了。人蛇对峙良久,忽然想到蛇应该是下河喝水的,并非冲我而来。但互不相让如何是好?想起书上看过的一句古话“狭路相逢勇者胜”,顿时有了主意。便从背上抽出那把遮风挡雨的大红油纸伞来,撑开了,一边呐喊一边朝蛇挥舞。我只听说鬼怕红东西,野兽怕火,狗怕打狗棍,至于蛇是否怕,听不听得见,看不看得到,情急之中想不得那么多了。谁知这招竟有效,蛇也愣了神,低垂下头细细打量思忖:不知面前这团红东西又是大喊大叫,又是手舞足蹈的,竟是何怪物?看来它也没想明白,算了,不想了,三十六计,走为上!一矮身子,从我身边的峭壁上擦身而过了。我还管它喝不喝水,伞也不要了,打起飞脚,好一似侦察英雄杨子荣一口气又跑上了威虎山。回到三叉路口,从那条毛毛路直下,真个是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心里才明白,那条石板路是社员下地的路,毛毛路才是乡道,不过因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社员又都忙着学大寨下地干活,没时间走亲戚,往来稀疏,竟把大路荒废了,心中不禁一阵感叹。
如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与蛇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蛇们也在与时俱进,越来越怕起人来。
前年我回队上去行亲(行读hén,湘西话,行亲就是走亲戚的意思),因村里还未通公路,六七个好友执意要送我到十五里山路之外的省道上赶车。有二舅、四舅、三哥、海妹,还有大治,一行人行色匆匆,翻山过岭,顾不得留意两旁的景色。翻过一个垭口,忽闻一阵响动,就见坎下草从中齐齐分开一条路,草倒向两边,怕是惊动了一条晒太阳的蛇,落荒而逃。还没看清楚,只见大治像狼牙山五壮士一样勇猛,从陡峭的偏坡上奋不顾身地跳将下去,嘴里喊着“跑了!跑了!”说时迟那时快,已经追到了蛇的身后,右手操住了蛇尾巴,趁蛇一扭头来咬,左手“唰”地就熟练地捏住了蛇的“七寸”,真是好身手!绝对超过《捕蛇者说》里蒋氏的专业水平。大治逮着蛇从坡下爬上来,一脸洋洋得意。那蛇看样子是又惊又怕,只怕是肠子都悔青了,可怜兮兮地在他的手梗上扭曲成一团麻花。几位乡亲都羡慕地望着大治,三哥说:“好财喜!少说有两三斤,逮到镇上立马就兑得钱”,大治笑答:“可惜是条菜花蛇,要是条白花蛇、最好是烙铁头,那就值钱了!”
哎,如今不论城市、农村,蛇是越来越难看得到了。农药、老鼠子药,还有挖掏捉打,人类的本事越来越大。看这架势,到我孙子那一辈,除了动物园、养蛇场还有就是蛇餐馆,他们要想看活蛇是不大容易,要像我一样有丰富的斗蛇经历就更难了。转念一想,也好,对小孩子来说,安全第一,省得像我做细伢子时候那样为了蛇担惊受吓。
二○○七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