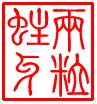偷粪记
—陈乃广作
二十多位来自江永县各公社、农场的知青,离开了各自熟悉的群体,聚集在离县城七里地的接龙桥旁。那是1965年初春一个阴霆寒冷的日子,江水农艺队在这荒凉的角落里诞生了。
附近大队将靠山边的三十多亩贫脊荒废的水田和十多亩杂草丛生的旱土拨给我们。春耕开始了,田里地里急需肥料,怎么办呢?有人提议到县城各单位的厕所里去掏粪。队长将此任务交给我,我想整日站在水田里多难受,每天跑县城几好玩啰,欣然接受了挑粪队长的重任。从那天起,只要不下雨,我每天带领一、两名队员去县城寻找粪肥,留下了难忘的挑粪史。
当时县城各单位的厕所都被附近生产队承包了,很多粪坑口还加盖上锁,严防偷粪。
我们麻着胆子,担着粪桶偷偷摸摸溜进县委、县文化馆的大门,因为那里的门卫常看我们演出,多少有些面熟,见是农艺队的知青来了,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放行。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县农业局、林业局、银行、医院、农机站、粮站等单位都留下我们的足迹,而且上天保佑,每天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你莫小看偷大粪,粗活里面有学问。当时我把偷粪经验编成项口溜:揭盖开锁,先套后撬;锁打不开,铁扣拔掉;硬是不行,就用粪瓢;蹲位里掏,角度维妙,斜进平出,很有诀窍;摘水不漏,恢复原貌;不留痕迹,尤为重要:以图下回,考虑周到。
经过一个多月基层摸底,我们对县城十几个大小厕所了如指掌。就说粪的质量吧,县人民医院用水多,粪池内清汤寡水,肥效不高。县银行,文化馆职工少,粪源不足,供不应求。唯有县粮站取之不竭,质量上乘。一是因为粮站职工“近水楼台先得月”,吃得多,拉得多;二是因为每天有很多农民排队送公粮,从早到晚,人来人往。农民早上吃的南瓜红茹,绿色食品消化快,肩挑重担走十几里路,放下担子第一件事就是要方便,因此十几个蹲位的厕所总是人满为患。
到粮站打粪要从厕所后面一个两尺高的方洞里钻进去。每次我们都会礼貌地大喊一声:“有人吗?打粪的来哒!”听到上面有人踩得木板咚咚直啊,估汁都是提着裤子跑开的。我们这才将粪桶放进去,然后弯腰驼背钻进氨气刺鼻、令人窒息的洞里。昏暗的光线中我们许久才适应环境,抬头望去,上面的蹲位像一排天窗,光线从头顶射下来,只见粪坑旁有一条一尺多宽的边,刚好放稳一个粪桶,稍不留神就会连人带桶滚进坑里去。我们就站在“悬崖”边作业,装满一担,头昏眼花,全身汗透。出来时更不容易,满满一桶粪,足有五十多斤,我们先钻出洞口,跪在地上,将粪捅拖到洞口边,然后两手抓着桶耳端出采,此时嘴脸几乎贴着桶边了,但谁也没说过脏和臭。
我们的任务是每人每天挑两担粪。从农艺队到县城上下午来回四次,每天行程三十多里,天天如此,还真要体力。过去长沙有个粪码头,据说拖大粪的劳力叫吗子,不知谁先叫我“广码子”,接着和我一起担粪的汤小约为“约码子”,谭泽先为“谭码子”,后来农艺队的男劳力们均被授予“码子”的光荣称号。
记得1966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烈日当空,闷热无风。我和泽先、小约打着赤膊、穿条短球裤,挑着沉重的大粪行走在望不到头的公路上,公路两旁是刚种的小树,稀稀拉拉,无处停歇。我们大汗淋漓,利用背上的汗水转动扁担换肩,这样不会磨破肩膀,也让承重疼痛的肩骨轮换体息。我低头,舔了一下嘴角的汗水,双手托着扁担大声喊道:“码子们,坚持走到前面那根电线杆下!”心想此时口里要叫喊点什么才来劲,突然想起了长沙快板《南门口》,“提起过去南门口,冒事莫往那边走,一条小小麻石街,破烂担子两边排……”三人异口同声唱起来,顿时真来神了,脚步踏着节奏越走越快,完全忘记了肩上的痛苦。这段快板足有十多分钟,当我们念到“三十岁脸上皮打折,四十岁又转桃红色,枯木逢春发嫩生,今晚又当新郎公”时,己经看到农艺队的大门了。从此,我们凭着年轻好胜的狂热,经常挑上百把斤一口气走七、八里地,并引以为豪,殊不知落了个腰肌劳损病,永远陪伴我们一生。
每当我腰痛发作时,我眼前又出现那些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码子们。
二○○七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