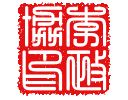1968年秋,百余名清一色的农民组成的“工宣队”,进驻了当时不足20名知青的江永县农艺队,不出几天功夫,即揪出10来名“炮打三红”的现行反革命。本人也在其列,且因秉性执拗,更是加判了莫须有的“判国”罪名。一个行武出身、五大三粗的民兵营长将我双臂反剪,一索子捆个绷紧,疼得我冷汗直流,压至县公检法军管会才松绑。此后又是一番例行检查,连裤带之类都收取一空,这才让我提着裤头走进三号监房。
三号监房的囚徒外出未归,我便趁此打量这囚房:五六寸厚的木牢门笨重而牢实,对面墙上有一铁窗,护窗铁条粗而且密,却无玻璃;靠窗左边墙角有一地槽式的坑道,供大小便用;进门右墙下,六米长三米宽的地板上一字儿铺着十多床被盖。左边墙上”坦白成宽,抗拒成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等标语赫然在目。据狱警训示,此乃晨起睡前必读之狱课。我入狱以后,见众囚徒履行此牢规十分认真,皆扯喉提嗓颂读不厌,初不明其故,久而方悟其妙。原来此举一则可表白各自接受改造之虔诚;二则对维持大声说话的生理机能实有助益;三则呢,一腔积郁籍此得以宣泄释放......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