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村文化际遇·
一九七○年春节刚过,我被安排插队落户到永顺县麻岔公社团结大队哈列湖生产队。这是一个土家族聚居的村寨,但已经没有人会说土家语,许多年以后,我才得知“哈列湖”的意思是狗喝水的地方。族人的先祖于二百多年前避祸举家迁徙,途经此地,干渴难忍,四顾无水,幸猎犬发现一眼泉水,救了全家,遂就此伴水定居,至今已有十余代,其村落也因其得名。当地人多姓郑,恰巧我母亲姓郑,于是我便称年长者为舅舅,平辈者为兄弟,加上我学说当地口音很快,刚刚走入社会的我不久便融入了这个第二故乡。
哈列湖实际是个小山窝,四面环山。百余口人分为两个生产队,二队居东边,居住集中,田土稍好,我在的一队居西边,居住分散,田土较差。七十年代初这里不通公路没有电,生产生活条件艰苦,基本保持着农耕文化的上古遗风。二队舍得送子弟读书,出了几个干部、老师,一队的成年人多是文盲,于是便出了许多与文化有关的趣事。一位乡亲去十余里外的石堤镇赶场,怕人瞧不起,穿戴一新,还特地
时间一长,我才明白哈列湖的文化不是用文字而是用口头来演绎和承传的,这种世世代代心口相传的传统文化的深厚瑰丽,令我惊叹。其主要形式当数山歌、哭嫁、摆龙门阵。队上的五嫂据说是山间对歌被五哥钩来的,不过从过苦日子以后,不大听得到歌声。五嫂被我求不过,唱过一段“五句歌”:“小小鲤鱼紫红腮,下江游到上江来,冲破道道青丝网,绕过座座钓鱼台,不为冤家我不来。”那旋律的委婉缠绵使人难忘。哭嫁歌给我的是另一种震撼。一天晚上突然听到下屋一片哭声,我大惊失色,一打听,才知道是一群十多岁的姑娘在学习哭嫁,这是她们的必修课,准备将来出嫁时哭别爹娘、兄妹、哥嫂,歌声和哭声饱含对故园的留恋、亲人的不舍,却也难掩对新生活的企盼。摆龙门阵是成年人主要的精神生活。老老少少围坐火坑,谈天说地,谈古论今,直到夜深鸡鸣,火坑中只剩几点余烬,才陆续尽兴归去,我从中长了不少见识。
山村的文化生活是贫乏的,盛事要数公社开大会和放电影。公社离村有七八里,开会的内容都记不起来了,村民们高兴的是趁机与邻村的亲友们聚会交流。最兴奋的是未婚男女青年,拣最好的穿戴打扮,看过来瞧过去,姑娘们三五成堆,说说笑笑,眼睛却总是往四处瞟。一年难得放几回电影,好比过节,好不好看倒在其次,昏暗中挤挤搡搡自有其乐趣。一路路火把伴着笑语在山间游动,把一天的辛劳和忧愁都驱散了。
乡亲们没几个识字,我这个高中文化的长沙知青也就有了用场,写个上面要的材料,办个宣传栏,用石灰水刷标语,大多是派给我的活计,我乐得又得了工分又练了字画。以后,村民的家事也找到我了,写家信,写对联,这点举手之劳的小事,他们的感谢总是溢于言表。我们大队的十个知青在劳动之余不甘寂寞,联络几个本地青年自编自演了几个小节目,简陋的服装道具,摇曳昏暗的松明火把,却是大受欢迎,演遍远近四邻八寨。看到他们专注的神情,我们深深感觉到:山村缺少文化,山村需要和渴求文化,我们总算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这使我们感到欣慰。
然而当时正在“文革”中期,扭曲畸形的政治文化环境,加上传统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使我很快就遭遇了挫折。先是队上按上面布置要办政治夜校,议好一二队合办,要我去当夜校老师。我把二队的一间堂屋打扫干净,在残存着“天地国亲师”的神龛上方贴上“政治夜校”的红纸校名,架好自制的黑板,当晚夜校开课了。男女老少来得不少,讲讲革命形势,学几个“人口刀尺手”,教唱一首革命歌曲,大家还算满意。第二天晚上刚要出门,本队的几个小青年跑来,支支吾吾地说好象有点不对劲。过去一看,黑板上歪歪斜斜写着一副对联:“乡有才当灰烬,远水客作秀才”,横批“政治夜校”。那时我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即刻把两位队长请来做主,他们关起门来商量良久,结果是改为各队自办,我仿佛火坑里浇了一瓢凉水,再也提不起精神。
更没想到的是,缺少文化的农村也会有文字狱。公社书记路过,在我办的宣传栏前看了半天,忽然皱着眉头说:“这个‘广大贫下中农’的‘大’字怎么少了一横,这不成了‘广人贫下中农’?!”唬得赶来作陪的副队长赶忙作检讨:“领导批评很重要,我们对知青管教不严,马上改正。”书记从火坑里抽出一根柴棒,在短了一截的一横上添画了半截,哼了一声扬长而去,于是我的厄运开始了。先是宣传栏被揭了下来,然后私下传得沸沸扬扬,说我写的是“管制贫下中农”,出身有问题的知青要到农村来反攻倒算了。不久我的夜校老师就被撤消了,政治夜校也不了了之。
祸不单行。当时正是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本队因为没有地富反坏分子,大队特地从别队调过来一个姓周的伪保长,作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开会由他送柴生火,躬腰挨批判。此人读过不少古书,自视甚高,但村民和我都从不搭理他。也是合该有事,一天傍晚收工,我们一前一后,赶着牛,扛着犁,走在一条山脊上,正是雨后斜阳,山色苍翠,空气清新,风景如画,我不禁脱口吟出《滕王阁序》中的句子:“云消雨霁,彩澈瓯明”,周保长猛一回头看我,接口道:“落霞与孤骛齐飞”,我也顺口接上:“秋水共长天一色”。两人无话,各自归家。谁知这周保长到处说:XX真有文化,熟读古诗文。这还了得,经过几晚没叫我参加的贫协会后,贫协组长神情严肃地通知我参加批判会,当看到周保长躬身站在台前,贫协组长宣布追查阶级敌人借古讽今的反动言论时,我眼前一黑,心想这回在劫难逃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声色俱厉的批判,我惊异于他们的政治嗅觉,我怀疑背后有高人指点,否则怎么会分析出“落霞”指地富反坏,“孤骛”喻知识青年,秋水长天同叹命苦,一唱一和,心怀不满。轮流发言后,只剩下我的房东一声不吭。因他是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前任贫协组长,在队上又排行最老,有一言九鼎的威望,所以大家都催他“逮两句”。他钩着头吭哧吭哧抽了半天草烟,突然抬起头来吼道:“逮、逮、逮什么逮!”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会场一片沉寂,村民陆续开溜,批判会就此草草收场了。几天后正式定性:这是反革命分子拉拢腐蚀知识青年的事件。周保长自然罪加一等,我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理。去年我去看望房东老舅,八十多岁的他已经卧床多日,听到我的声音,爬起来欢喜地说一声:“你回来啦!”喝了一大碗酒,又蒙头睡去了。
那段时间,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沉默寡言,埋头出工。我学会了抽烟,把带来的书本撕掉,分给村民们卷了喇叭筒。许多人感到了这种变化,感叹说村里不热闹了,我只有报以苦笑。当我从消沉中重新振作起来,用我的文化知识为村民做点事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抽调到铁路建设文工队,从此走上工作岗位。当我离开哈列湖的时候,回望山村,心里有一个声音:那里有过我的酸甜苦辣,那里有过我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我还会回来的。
岁月悠悠,三十多年过去,一幕幕往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回顾反思,山村最缺的是什么?缺条件、缺钱,但最缺的还是文化。这些年虽然有了公路、电灯、电话、电视机,队里却还是没有出一个高中、大学生,生产方式没有变化,产量没有增加,品种没有更新,种烟、果树、药材样样不成功,出外打工只能干插秧打谷摘棉花砍芦苇这些最苦最累不挣钱的活。没有文化知识,没有科学技术,怎么会有腾飞的翅膀?
第二故乡,我们还能为你做些什么?我资助乡亲们退耕还林、买变压器立电杆,但我最希望做的还是扶贫助学,遗憾的是我资助的两个学生没读到初中都辍学了,只有一个二队的女孩争气,考到长沙念大专。我真诚地希望山村不要再成为被现代文化遗忘的角落,让文化的光辉照亮山村的前景,照亮乡亲们的脱贫致富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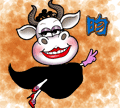





















朵朵:我曾经有一次步行到永顺与龙山的交界地,后来修枝柳铁路时去过龙山县城好几次,还到过洛塔---一个很有特色的山村。湘西的山水美,下放的知青多(光我们永顺就有长沙知青500多人),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为什么湘西知青不把自己的网上家园办起来呢?我相信那会有更充分的交流和共识。你是版主,期望能为我们建立起一个平台。
回病牛;原来申请过开湘西知青专栏,因条件不成熟,主要是上网的湘西知青少,就作罢了,现在你来了,而且永顺是从学校成批下放了那么多知青,不象我们龙山,只有十几个随户知青.条件成熟了,我也觉得可以开湘西知青专栏了,而且你任版主是最合适的了,我们共同向笨笨牛总版主申请吧.
我已给笨笨牛总版主发了短信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