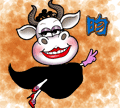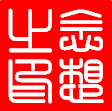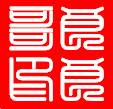怀念娭娭
一提到保姆这个词,我眼前就会浮现出我幼年的保姆——娭娭(谐音字,长沙话里奶奶、婆婆的意思,以下同)的慈祥面容。那时我四岁,家里又添了个弟弟,母亲便想请个保姆。连着试了好几个,我们兄弟都不理睬,直到那天娭娭走进来。我懂事迟,五岁以前别的事都记不起来了,却清楚地记得,娭娭走进来,五十多岁,系条腰围裙,慈祥的笑容,结实的身板,和蔼的嗓音,好象很熟悉地就把襁褓中的弟弟抱在怀里,而我就扑过去抱住她的腿,无师自通地叫她“娭娭”,当时还并不知道在长沙话里娭娭就是“娭毑”(长沙话奶奶的意思)的昵称。听得大人们说:“这婆婆跟孩子们有缘,就是她了”。从此以后的四年中,娭娭就成了我们家的一员了,好象本来就是家里人。母亲经常出差不在家, 娭娭就是当家人,母亲的工资归她去领,柴米油盐一应家务也由她安排。那时候还没有《劳动法》,也不兴休息日,平日忙里忙外,听人带信说家里有事,才告假回去一趟。
娭娭姓陈,丈夫早逝,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女婿子女多生活困难,娭娭只能出来做事赚点钱。那年月其实家家都不宽裕,做保姆的工资很低,除了包吃住,每月大约是五、六块钱。她拿一部分补贴女儿家,自己也留一部分作用。说起来,娭娭每月的用项还不少。首先,她要吸烟,那时候很少有人抽现在的卷烟,更没有过滤嘴,绝大多数用水烟袋。娭娭的黄铜水烟袋总是擦得锃亮,后部烟筒装满烟丝,中部插着纸煤子和剔签,烟道剔得干干净净。她忙碌完了就坐在矮靠椅上拿出水烟袋,悠悠地装上一袋烟,然后眯着眼“噗”地一声吹着了纸煤子,赶快把火凑到烟丝上,含着烟嘴,只听见“咕噜咕噜”一阵轻响,娭娭饱经沧桑的脸上便泛起惬意的神情。看得有味,我曾经偷偷试过一口,不曾想吸了满口的烟袋水,又苦又辣,呛得我换不过气,好多年后想起来还作呕。娭娭的第二个嗜好是看花鼓戏。她只喜欢带我去看,我听说去看戏总是很兴奋,坐进戏园子,听着锣鼓家什一片响,等不及大幕拉开。可真开了演,穿着花花绿绿戏服的男女咿咿呀呀地唱着些听不懂的词扭来扭去,又不打仗,娭娭她们大人却看得津津有味,我的眼皮就不自觉地打起架来。总是在娭娭背我回家的背上醒来才知道戏演完了。娭娭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敬菩萨,我最记得清楚的是过小年送灶王爷上天。吃过晚饭收拾停当,娭娭在灶台前点起三柱香,摆上几个碗,一个碗里是木炭,另一个碗里是娭娭自己出钱买来的供品——长沙称为“猫屎筒”的一种最廉价的糕点,就是它勾引得我已经吞了半天口水了。娭娭虔诚的叩了头,又要我也叩头,我赶忙重重地连叩三个响头,因为我知道下面就是娭娭念叨些“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之类的话,然后就是把供果分赏给孩子们了。因为我的头叩得最响,每次分给我的最多。成年以后,我曾多次买回这种长沙特产回味,但再也没有吃到过幼年那样好吃的“猫屎筒”了。
那年月粮食要计划,我家又四个小子,饭是永远不够吃。每次吃饭,娭娭总要等到最后,剩下多少吃多少。娭娭对我们兄弟总是“恩威兼施”,遇到我们不听话,就扬起手里的大蒲扇做出要打人的样子;乖乖听话写字、画画,就从腰围裙里掏出一把带着体温的蚕豆、花生分给我们。到了五六岁,还是娭娭每天把我扯到大脚盆里洗澡。我喜欢她用温暖而粗糙的大手在我身上搓揉。但是我有个怪毛病,一洗澡就想撒尿,懒得擦干身子穿上裤子去茅房,我就悄悄地把尿撒在脚盆里。那可得有点“技术”:只能坐在水里,憋着尿一点一点的撒,那个舒服呀,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的神气,否则就会露馅。娭娭就用我的尿水给我洗了好多次澡,至今想不明白是我的技术真的高超,还是娭娭故意不戳穿我的秘密。
我第一次到农村是娭娭带我去她乡下娘家,坐长途汽车去的,那年月的长途汽车是个木头车厢,后面开两扇门。娭娭的弟弟用独轮手推车把我这个城里贵客送到车站,汽车开动了,车后“突突”地冒着浓烟,乡村土路扬起漫天尘土,烟尘里他追着跑了好远,从后车门里递上来一把小小的木靠椅,那是送给我的礼物和纪念品。这把靠椅我们家用了好多好多年,直到它油光发亮,泛着古铜色光泽,仿佛人的皮肤,还带着体温。
虽然娭娭不识几个字,只能教我们唱唱“月亮粑粑”一类的儿歌,但小时候我总认为蔼蔼是最有办法的。一次,我和弟弟坐在火炉边烤火,炉子上架着烘罩,上面又盖着小棉被,不知怎么的就着火了,我被吓得又急又怕,不知所措,娭娭操起盛冷开水的大茶壶一阵就把火浇熄了。她麻利地把家什都重新收拾好,却没有责怪我一句,我真是又感激又佩服。
不知不觉中,童年的我在娭娭的呵护中长大。1957年我8岁,因为母亲被下放到远郊的工厂,只好卖掉老屋,举家搬迁,娭娭不能随我们同去了。那几天家里笼罩着静默,母亲和娭娭都不出声地清理东西,直到那个寒霜的早晨,母亲牵着雏鸡般的我们四兄弟走出家门,低头哽咽擦着泪水,送出门来的娭娭沙哑着嗓子在身后叮嘱“好生走啊”,此时此刻,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人生自古伤离别”。娭娭叫她当搬运工人的女婿把我家的家具堆了一板车,翻过黄土岭、金盆岭、豹子岭,送到了几十里外的新家。记得她女婿叫黄春生,一个壮实而和善的汉子。
分开没几年,就听说娭娭去世了,只留下一张照片在她女儿德姐姐家挂着。我们两家后来还继续走动了好几年,好象谁也没有计较谁是什么阶级成分,直到“文化革命”开始。记得德姐姐有次到黑石铺来看我们,用一块大手帕提着一兜子鸡蛋,我真佩服她的本事,颠簸几十里,满兜鸡蛋居然没碰破一个。
人生真叫“白驹过隙”啊,娭娭与我天人两隔转瞬已五十年,我也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祖母和外祖母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早已模糊不清,只有娭娭的音容笑貌还是那么清晰,栩栩如生。回长沙后我特意到老宅故地去探访过好几次,老房子早已荡然无存,连那条叫“宜兰园”的小街也早成了历史,附近高楼的住户都摇头不知道,也不知娭娭的后人搬到何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