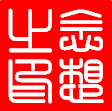当年老爸不幸触“雷”,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送劳教,娘老子那一鹅毛筒工资谨能一家人勉强维持生计,为哒补贴家用和赚学费,老妹她们糊火柴盒,选瓜子。我作为家里的小男子汉,只好跟得一些贫苦人家的细伢子一样,出克“逞”板车。
记得那时候西湖桥靠猴子石那方向都是砂石码头,每天是川流不息的货车、板车搬运砂石,侧边还有一个大的垃圾场。灰尘中,冬日下,翻垃圾的、衣着褴褛要饭的、逞板车的,各色人等,林林总总。我也间常参杂其间,带一双纱线手套,“忉”一件旧抹哒的烂棉袄,两边交叉往腰前一紧,一手托哒咯扎下摆,脚只咯踮,肩只咯耸,小小年纪也学哒带点流气的话尾子,只要看见搬运码子拖出一车砂子就喊:“加油不罗!加油不罗!”“试一哈噻!硬腿赖!”周围也是一片喊声。搬运码子有时候“扳翘”,虽然还冒上坡就汗直个统,还是装做爱理不理,一群人就跟在后面追哒喊,甚至扳他的车子,直到谈妥一桩“生意”,人群一哄而散又缠后面的车子克哒。
刚开始年龄小,从西湖桥码头一直逞上天心阁只有五分钱,后来涨到一角、一角五。再大一点又跑到南站克逞煤。那时火车南站是个煤站,从南站拖出来的煤背靠湘江向三路辐射。往南上金盆岭,往北去雨厂坪(冶金厅),往东上碧黄支线(碧湘街至黄土岭专线),就是现在的南湖路。碧湘街在雨厂坪下面,与黄土岭天隔地远,至今还搞不清俄改要喊碧黄支线。南站一面靠水,三方是坡,是逞板车的福地,碰哒寒暑假我一逞就是一个假期。因为舍得卖力,加之谈“生意”渐渐的老练、麻利,在逞板车的“老少爷们”中间已小有“名气”,大嘎都喊我“猫贩子”,就是会钻的意思,别人逞金盆岭一上午只逞得两三个来回,我最多逞过五个来回,那时逞一个金盆岭两角五,接过工钱飞步下坡,又接第二车,一天下来也确实可观。后来有哒“回笼头”,碰哒熟识点的搬运码子就搭他的“回笼头”下坡,咯样就省力多哒。不过逞煤不象逞其他货物,经常是搞得一脸一身乌漆抹黑,只看见雪白的牙齿和骨碌乱转的眼睛珠子。热天还好,旁晚跳得河里一洗了事,冬天就只有捱得断黑偷偷回家,把烂棉袄脱嘎往床底哈一塞,洗把脸睡觉。如果逞的路程较远,错过哒恰饭的时间就随便在外面买点家伙恰,逞板车最忌口干冒得水恰,因此一到目的地,也不管是厂矿还是机关,首先是找哒自来水笼头咕咚咕咚灌扎饱,久旱遇甘霖,那种感觉真是荡气回肠。最爽的时刻当然还是带着满身的煤尘和疲惫数钱的时候,数着一叠叠沾着汗水和煤尘的皱巴巴的角票,那种高兴劲更是无以复加。一直到初中毕业下农村,我在读书其间陆陆续续打零工逞板车,很大一部分学费和一些衣物用品都是用自己的血汗赚来的,也幸亏曾长期逞过板车,我有幸成哒知青中最能够适应生存环境的那一类人。
很多事物就是咯样不好理解,我在过去的年代历尽劫难,又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可我的命运又总是贯穿着一条不畅的主线,我到如至今还是冒搞熨贴,我咯一辈子到底算幸运还是算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