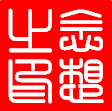二、报纸夺命
一九七0年三月六日,是我下放靖县告别长沙的日子。这一天,父亲单位的子弟只有唯一的我要去到靖县。我是到长沙纺织厂集合后乘专车离开长沙的。
头几天,母亲为我准备全了行头。六日这天,终于要离家了,我却有了强烈的不舍之情,心情有了些许道不明的沉重。在浏阳磷矿工作的姐夫这天也刚好来家,几个女同学好友也相约到家来送我。姐夫在一旁反复问我:“不去靖县去浏阳行不?”只要我答应,他就回浏阳帮我办手续。我不表态,用沉默坚持着要去靖县。
母亲给我做了较丰盛的中餐。我低头嚼着母亲做的可口饭菜,听着母亲的絮叨、叮咛,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强忍不舍之情,不敢看母亲,不敢与她对话,我怕自己会失控,我不想当着同学的面伤心流泪,不想让同学看到我的软弱一面。就这样,只到饭后离家,我始终没有给母亲留下只言片语。在同学的陪伴下,在弟妹的相送中,走出家门很远,我竟一直没敢回头,没敢再看母亲一眼,没有表达我对母亲对家的依恋之情,没能将我心底那份对母亲的挚爱倾泻出来。留给母亲的是心存失望,心存不解,她最疼爱的女儿远行前为什么这样狠心,这样决绝......我哪会料到这一分别,竟是与母亲的永别啊!这一别,使我留下了终生对母亲的歉疚与追悔,在心中留下了一份永久的沉重的伤痛!
多少年过去,每每想到这些,我就会抑制不住伤感悲切,总会有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悔从心底涌出来,我在心底里无数次责骂过自己,我痛恨自己。那个年代,母亲那时侯心里有多苦啊!我没能理解!我离家时没有留给母亲丁点儿温存,没有给母亲半点儿安慰......倘若我离家时,能对母亲说上几句温情的告别话,能再多看她几眼,能再多叫几声——妈妈!也许,我的母亲在后来的那十几天内,对那些恶魔的淫威会采取另外的抗争方式,是不会丢下我和弟弟妹妹的......她会知道女儿我是多么需要她!我不能失去她......
我父亲和母亲那时是怎样要走绝路的,家里人唯有我不很清楚这其间过程,我至今也没详细问过谁,我不愿也不能揭家人心中这道伤痕。我家的这些事那时在河西SCJ是很轰动的,外人都比我知道得多。我除了从姐姐信中知道母亲的去世消息外,其他情况多是听别的知青或同学告诉我的,离开农村进工厂后,回家也偶尔听妹妹和一些邻人说过一些。
我离开长沙后不久,父亲单位要将我的家人遣送回父亲老家,父母亲也同意了走,并着手清理家什做搬家的准备。他们在做搬家的准备!他们是根本没想过去死的!
我家爱订些报刊,众所周知,那年月的报纸期期几乎都有毛主席和林彪像。母亲将报纸清理作废品卖,就有那些惟恐天下还乱得不够的该永远受良心谴责的好事者、无耻阴险小人,将我母亲卖废品的情况汇报,以此而邀功请赏。单位上迅疾来了一群恶魔,指责我母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竟敢将“毛主席和林统帅”当废品卖,是罪大恶极,是罪不可赦。又要将我母亲拉去批斗,还要狠斗我父亲,再押送去乡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善良的母亲哪里担得起这样的罪名,哪能承受得起这突如其来的比天大的祸端。挨批斗虽是家常便饭,现在又突然被加上一顶压得人死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并要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押送去乡下,母亲的尊严,母亲的脸面将丢失殆尽。这是强加给她的奇耻大辱,她不能带着这耻辱回老家,绝境中的母亲肯定还想了很多很多......母亲善良坚忍,一生历经艰难坎坷,她生养了七个儿女,不是恶魔们逼人太盛太狠毒,她是不会轻易抛家抛子走绝路的……父母亲商量了,与其苟且承受这些无穷尽的屈辱,不如以死抗之,死也死在长沙!
父亲和母亲实施了他们一起赴死的行动。有一天,不知是白天支开了弟妹,还是晚上趁弟妹睡着了,他们用电线缠住了自己,可能因电压不够,这一次,他们没有死成。
他们没有放弃死,紧接着又酝酿了第二次死的行动,他们决定了分开赴死。又一天,父亲带着我的弟弟妹妹到了河东二姐处,将弟妹交付给姐姐,说他要去处理别的事。姐姐感觉父亲行为有些反常,不放心父亲,父亲到哪儿,她便一直紧跟到哪儿。父亲最终说出了他是打算去卧铁轨了断自己的,并凄然地告诉姐姐,我母亲在家里可能已出事了。那时,长沙的河东河西往来必须乘轮渡。等他们再赶回家,母亲已经凄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永远离去了!
一辈子善良的母亲就是去死,也要保持着自己的善良。死后的她,嘴是闭紧的。别人说她死后的摸样一点儿也不吓人。母亲心中至死都是装着别人,总是替别人着想,连死都选择宁愿自己痛苦难受地死,不让死后的模样吓着别人!我母亲的死,是何等的惨!恸!
那个人妖颠倒的社会,那个黑白难辨的的年代......几张破报纸,轻而一举地夺去了我善良慈祥可敬母亲的生命!
恶魔们对我母亲的悲惨离去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心,还叫嚣我母亲是畏罪自杀,是罪有应得......没有一点儿人性的他们,不容我家人对母亲有任何祭奠,将尸骨未寒的我母亲放在一张竹床的反面,匆匆送到火葬场火化了,连骨灰都不让我家人得一把。并迅疾将我父亲和我弟弟妹妹赶出了单位,赶出了长沙,赶到了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