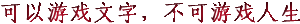写给四十年的纪念
1966年9月23日,我默默望着西去列车的窗口……弹指一挥,廿载!
1985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信函寄到西北我所在单位,朋友们说,这次你该返城了!我也似乎意识到,该返城了!
祖父说,他人生的前二十年在故乡,后二十年在国外……我的人生或许也是漫漫二十年为一个周期!1986年8月,我终于坐在单程的东去列车上……我的农村户口也终于轮回到曾经生活、读书的城市。
又走过了人生的漫漫二十年,转瞬间到了2006年秋,我应该为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写一点纪念的文字了。
一、我的1966年夏秋
那一年我正读高三。5月毕业考试结束;6月中旬,仲夏,“高考制度”废除了。
6月初,《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之风盛行,学校是重灾区之一,批斗老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邵淑惠先生是我的中学校长,其夫王金鼎是市级主管教育的领导,因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丈夫的“功劳”,自然有妻子一半,校长在劫难逃。学校文革前高考成绩是不错的,校长曾经以历届高考成绩自豪,这当然又成了文革开始后的主要罪证之一。 批斗会上打倒校长和她丈夫的口号声,震耳欲聋。红墨水、蓝墨水,从眼镜片上流下来,拳脚加在她单薄的身上。
批斗老师也愈演愈烈。老教师们大多是解放前大学生,很少有成分好的。数学老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臭小姐,沥青之类涂抹到被剃光了的头上。语文老师上课曾经涂脂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臭思想,需要好好改造!她被逼迫到学校楼房二三层间外墙、一砖多宽窄的地方走一遭,浑身打颤……
又有传来消息,市一所男子中学批斗老师够水平,学生们立即去取经。偌大的操场好像在吊丧,若干长长的白色魂幡在晃动,幡下也是一片白色,“牛鬼蛇神”们穿着丧服,敲着锣,转着圈,一片乌烟瘴气。真让人望而生畏。红色恐怖,“革命”风暴,席卷天地。这样,我所在中学被认为批斗力度不够——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是不能温良恭俭让的!
红卫兵冲出学校、涌上街头,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批斗也接二连三降临到同学们父母身上。一位同学父亲是铁匠,公私合营以前有个小铁铺。是不是有一两个小伙计,我不清楚,反正是有个小门脸,楼上住家人,她兄弟姊妹10几个。小私有者在那时候等同剥削者,他们的家什,被红卫兵从楼上窗口抛了下来,堆放到十字路口正当,又被点燃,纸簿被认为是“变天帐”!大火熊熊。同学的长辈们,都被逼迫跪到筚拨作响的火堆旁,满面通红,几乎烤出油来!那一幕我刻骨铭心。
另一位同学。父亲是小资方,那时只要公私合营以后拿利息的,都是资本家,哪怕拿一盒纸烟钱的利息!同学的父亲老实巴交,红卫兵找不出他的任何罪状,就成了“反动”资本家的陪斗。批斗会很多,陪斗也很频繁,他胆战心惊,难以禁受耻辱和煎熬。在一次批斗会之前,悬梁了!那时候,自杀就是抗拒革命,灾祸又降临到同学母亲头上,母亲没有了工作,一家四口失去经济来源。不仅如此,剃头、扫街,没完没了的体力、精神折磨……当同学的母亲故去的时候,同学也因病住院,母亲病故的噩耗传来,她不顾一切从医院奔跑回家,晕到在另一张床上,被伤心欲绝的同学们抬回医院。后来,这位同学也离我们而去了,是班里第一个离去的。她学习曾经很出色……
我所在中学校舍,曾经是民国要人曹锟在天津的府邸。气派的三楼一底西式洋楼,(在唐山大地震后不复存在了,我竟然没有留下学校全景照片。)文革开始以后,地下室就成了“黑五类”写检查的地方。我的罪状是父亲在国外,在国外的罪名一律是“投敌叛国”。检查一遍,又一遍,被认为不深刻,不彻底。怎么深刻呢,在国外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背叛祖国,投敌叛国!似乎是科学的等量替代,不知道合乎什么逻辑学。每天从早到晚,只能做一件事,写检查,写检查!学校一次次组织全校同学去北京见毛主席,我没有资格;到全国各地串联,也是不可能的。我十几岁的心灵,不知道曾经承受多么大的压力!阴森森的地下室,写不完的翻过来倒过去的检查,要上纲上线!万般无奈,我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
父亲在国外,不可能被揪斗了。我十分担心母亲,怕她像同学父母一样惨遭劫难。然而天佑母亲。母亲所在工厂前身,是广东人开的贸易行,招收的大部分是老广,几乎家家有海外关系。母亲又不是资方,所以,没有像我一样写检查。从科室干部下放到“要害部门”食堂劳动!
8月26日红卫兵冲击市委机关,9月18日,由市一中等16所学校在体育场召开揭发市委大会。19日传来消息,万晓塘书记自杀身亡,有花圈悼念。据说是服安眠药,死在澡盆中。 (文革后的材料说万书记是因心脏病暴发猝死。)
1966年夏秋,白色恐怖达到极致。
在十二分抑郁中,同班同学告诉我,某区正在报名去兵团,她可以替我办手续;我心动了,似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上山下乡,学生们情况不尽相同。有的是年轻人火热的心,支援边疆,“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有的主要是因为政审不过关,前一年中考、高考落第,上山下乡算是一条出路。有的是被“动员”,日以继夜,三番五次,熬不过去,等等。我又是一种情况,在地下室写检查,无日无月,无休无止,实在忍无可忍了!
去兵团,我政审不合格,也不敢过问办的细情,总觉得自己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怯怯的、惴惴的,似乎是落荒而逃。这种担心在上车之前、上车之后,以致最初到西北的日子里一直持续着。退城市户口的时候,万般无奈的母亲,没有说什么。
即将离开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城市,前一天晚上,我独自来到城市的母亲河——海河边。看着倒映在水中的几点惨淡灯光,思绪随着脉脉的流水,跑得好远好远。
我怀念读了六年书的母校和高中三年所在班级。我的班级,自认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我的高三三班是女生重点班,全面发展,样样争先,各级奖状挂满一面墙壁,大家的心太齐了。记得学校操场不大,每次上体育课,都列队到附近的体育场去。几百米路程,不需要喊口令,后边的同学随着前面同学的脚步,齐刷刷地走到体育场,曾经投来多少赞许的目光。如果高考制度不废除,又会如何呢……甚至高中毕业都没有机会留下一张合影……(在改革开放中,母校再次振兴了!2000年,50周年校庆,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老校长来了”!“老校长来了”!随着礼堂爆满的欢呼声,白发苍苍的老校长,在学生们的搀扶下,款步走到师生们中间,微笑着向大家频频招手,学生们高举鲜花跑上前去,校庆的热烈气氛鼎沸。望着熬过劫难,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我真是百感交集。又令我欣慰的是,我们班中不少同学文革后又上了大学,而且不乏成绩卓著者,这都是后话。)
快乐的童年、幸福的少年,一切,一切,都好像那么遥远了。远得好像是幽暗的河水尽头,远得好像是苍穹神秘莫测的星星。面临自己的将是什么,茫然无知。生活会是很艰苦的吧,不论如何,肉体的恐怕比精神的容易熬过吧。
第二天,1966年仲秋的一天,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把自己的肉体连同灵魂一起放逐了……
转自《老三届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