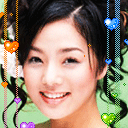重读《老子》 (一)
旧居读信
因为上了刘固盛老师的课,所以又有了重新阅读经典的欲望,第一本便是重读《老子》,读后大吃一惊。在陈鼓应先生《老子注译及评介》一书的扉页上我这样写道:“2006年11月27日听刘固盛老师课后再读《老子》,收获更丰。30岁读《老子》与23岁读《老子》,所感所获已然不同”。
喜欢尼采的评价:《老子》“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
1、《老子》第一章:“此两者(‘无’与‘有’),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一个“玄”字就将许多入门观看的人吓住了,在《老子》的门外伸头望了一望,吐了吐舌头,便缩回到世俗人生去了,岂不知《老子》的话如此浅显易懂,用的是简单的余言,谈的是简单的哲理,只是后人因为做不到,从而觉得它“玄而又玄”了,今天来看,哪句话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至理名言呢?可哪句话又是我们实践着的呢?我们用老子的“玄”将自己划出了该遵循的法则之外,这个“玄”,成了我们跳出老子之言的借口。
2、《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这个“仁”是指不与人同性,不同于具有情感的人。即指出天地是自然的、物理的。这个观点显然已经具有了自然哲学的意味,将“天”与“地”变成了客观的自然物象。这显然是春秋时期“天命观”变化的一个重要表象,与《诗经》中个体的歌咏,《春秋左传》中对人的肯定,《论语》中对“天”的怀疑是相辅相成的。可贵的是,《老子》不仅仅是怀疑,而且还彻底地否定了“天”的意志,现在想想,在那个刚刚脱离神的桎梏的时代,这是怎样的难能可贵。
3、《老子》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天长地久”,这四个字现在成了我们追寻的一个理想:追寻爱情的天长地久,追寻生命的天长地久。这四个字也成了一个成语供我们时刻表述自己的愿望。可是,我们却忽略了这四个字的后一句话。“以其不自生”,老子告诉了我们何以能天长地久的方法,但是,我们往往把方法抛弃了,仅存愿望,愚蠢地去自己摸索追寻。为何如此?因为“不自生”太难做到了,不为己而活,谁愿意呢?于是“天长地久”也就在后世仅仅变成了一种理想,永远难以企及的理想。
4、《老子》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关于“身退”,陈鼓应认为“退”是敛藏,不发露,并不是要人做隐士,只是要人不膨胀自我。所以可见后来范蠡、张良等人都理解错了。陈先生认为,老子的思想中,丝毫没有遁世的思想,仅仅是告诫人们,在事情做好后,不要贪慕成果,要收敛,含藏动力。
我以为,陈先生一定是理解错了的。他只是从个人心理出发来猜想,毫不想到人之所以要“退”还有外界的压力。范蠡难道不理解老子么?张良难道不理解老子么?只是外界的压力使他不得不遁逃。无论是范蠡还是张良,如果还存在于勾践亦或是刘邦身边,即使再“收敛”,恐怕也逃不脱这两个“狼颈鸟喙”之人的猜忌,遁逃才是最好的选择。所谓“敛藏之意”,恐怕是陈鼓应将世俗想的太美妙了,我想老子一定不然。老子的真感情,一定是要遁逃。遁逃也并非是遁世,而是“养生”的一个方法罢了。
5、《老子》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这显然是老子心中所想往的理想的精神圣地。
陈鼓应先生说,这是老子在本章中所流露的愤世之言。我不同意。读老子和庄子,我来没有读到他们的愤世情绪。老子和庄子的境界,早已远远超出了“愤世”二字。我们时刻说他们是善于“养生”的,是重“自我”的,尤其是《庄子·养生主》中对人在时间“游刃有余”的描述,根本看不到在乱世中半点愤世的情怀。再比如他对黑暗现象幽默的讽喻,比如“宋人舔痔”,比如“惠子相梁”等等,我们看不到他们“愤世”的自伤,只有幽默的嘲讽,他们绝无“愤世”之心。
6、《老子》第二十章:“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一定要感谢老子写了这句话。屈原的引用就姑且不谈了,只感谢老子。因为在自己的人生现实中,自己的精神境界与世俗无法通融的时候,这句话往往成了自己孤守的座右铭。
7、《老子》第二十四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这句与二十二章有相同之处。读后觉得,人本性很重要,后天的教育似乎作用不大。不谈普通民众,中国的学者读老庄、教老庄的恐怕不在少数,可是谁又真的听了老庄的话,“不自伐”、“不自矜”呢?又有多少人真听了老子的话,去关注“不自伐、不自矜“的人呢?老子的这段话显然已经成了人间世的另外一个轨道,在这个轨道上行走的人,少之又少,昏昏着,闷闷着。
8、《老子》二十九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王弼等人都认为“法”应解释为“性”.这样一解释果然高妙了不少。只是我有个疑问,如果这样解释,那么前面的几个“法”都该如此解释才好。都应解释为“人性地,地性天,天性道,道性自然”,可是这样解释又不通了。单单把“道法自然”中的“法”解释为性,高妙是高妙了不少,可是我却觉得不符前后文,对《老子》“高妙”的理解,这样似乎有点过于主观化了吧?仅疑存。
9、《老子》二十六章:“燕处超然”。
这四个字真诗意。
“燕处超然”,这是个怎样难以达到的境界,世人熙熙攘攘于浮华世界中谁能真正做到“燕处超然”呢?恐怕真正做到的仅有老庄和陶渊明三人,今也则无。现在这种境界已经完全成了后人无可达到的理想境地。孔子的“曲肱而枕之,不义与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显然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普通之语道出的普通之人不能达到的境界。我认为更多的中国人是没有此种本性的,正因中国人没有此种本性,所以孔子和老子才一味地追寻和呼吁这种人生境界。听到此种呼吁,听而不闻的,十之有三;听到此种呼吁,听到并且想力行,却在世俗中无可奈何的,十之有三;干脆听都未听过的,十之有三。
10、《老子》第三十章:“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这个“壮”,王弼注曰,“壮”为“武力”与“暴”。陈鼓应先生同意这个观点。我则认为,这个“壮”其实就是《周易》当中“大壮”与“小壮”卦中的“壮”。
11、《老子》三十一章:“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谓乐杀人。”
在这个思想上,老子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孤独的抗旗者;而老子的这个思想,在我们现世这个时代,也同样是一个孤独的思想境界。老子固守它,又怎能被他人所理解;中国人固守它,又怎能为外人所理解,更不要说采纳了。从这个意义说,这番语言,反而是“害人”、“害国”了。
12、《老子》三十三章:“强行者有志”。第四十一章又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亡若存;下士闻道,大笑之。”
“强行”即“勤行”。可见老子的“无为”不是指不去做,而是不妄为。所以老子一再告诫我们要“勤行”。刘老师将后一句作为《老子》这节课的结束语,我能体会到他是身体力行,并且希望我们也身体力行的,老子那种殷切的希望在刘老师这里得到传承。可惜,本身这句道,更多的人是“大笑之”。真正理解老子“勤行”背后的殷切之情的人,又有几个呢?
13、《老子》第三十八章:“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老子将人分成几个层次:最上为“道”,其次为“德”,再次为“仁”,再次为“义”,再次为“礼”。当今之人连“上礼”之人都算不上。对“上礼”之人的描述,简直太生动了――“攘臂而扔之”,后世有什么样的语言能比得上这样生动的描绘呢?恐怕只“燕处超然”和“攘臂而扔之”两句,就可以将《老子》看做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