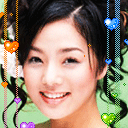66年,厌倦于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已经开始了全国的大串联.开始,我们还到高校去看看大字报,后来,这种惯性的动作中,注入了新的内容,即到全国去开开眼界.要知道,文革前,班上除开那些干部子弟(那是真正的高干呀)之外,绝大部分同学都没出过长沙市.还记得我班的一个同学,在学校足球队当守门,随校队到青岛去参加全国少年足球赛,曾把我们全班男生羡慕得眼睛里滴血.现在大串联,坐车不要钱,管吃管住还管穿,不出去跑跑,太吃亏了.于是,我就和一个同学一起,跑到了哈尔滨.
我们住道里区,兆麟公园附近.在哈尔滨,我们坐着公共汽车,从一个站的起点坐到终点,有时到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乡下,又再坐回来就是,反正不要钱.哈尔滨那时还有许多白俄,零下40多度还穿着裙子,令我们惊讶不已.在哈尔滨,我第一次喝了啤酒,吃了列巴(面包,俄文的译音),秋林公司的,啤酒一股马尿味(虽然我并不知道马尿是什么味道),一点味都冒得,至今我还不喝啤酒,可能就是那时种下的病根.在哈尔滨,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冷,早晨在房子外边嗽口,回房子拉门上的铁把手,手上的嗽口水就冻在了铁把手上,总觉得黏黏的;幸亏在沈阳借了东北的大棉裤,就是那种穿了,裤腰到了胸口,系裤带时要把裤腰折几下才行的扎头裤,我们才熬了过来.另外,哈尔滨满城的大树,坡度极大,高低起伏,且带有异国情调的大街,也给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极大的震撼.
40年后,06年暑假,我又到了哈尔滨.当年风华正茂的中学生变成了白发苍苍的半老头子,当年我印象中的哈尔滨又变成什么样了呢?我拍了两组照片,今天献给大家的,是哈尔滨市内的风景.
哈尔滨的啤酒节.第一张,虽然我不喝啤酒,但仍然有一个啤酒肚.第二张,街上运啤酒的马车.其实只是做样子而已,现在运啤酒早就是汽车了.第三张,啤酒桶的细部.

汽车\自行车和卖豆腐的毛驴车.这是在距哈尔滨中心大街(相当于长沙的黄兴路步行街)不到十米远的地方拍的.


索菲亚大教堂及教堂中的耶稣(?)像.我不信教,但我相信,让人有所畏惧,尽心向善总是好的.我很想到教堂里去听听唱诗班那圣洁的歌声.
兆麟公园.时代的英雄\满城的大树,已经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和眼中,然而,那种英雄神圣和古树苍劲,能让他就这么消失吗?
中心大街的画家们.真好,凭自家的本事挣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