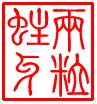我们农场撤销插队后不多久,纷纷有女同学嫁给当地农村青年。虽然不应当怀疑有爱情因素存在,但也使人感到有的似乎是不得已为之。几个最先嫁给农村青年的,大多本身条件较差,劳动能力也偏弱,又因为家里也是长沙的较贫困人家或是继母当家,她们从家庭似乎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和温暖,只得在农村寻找归宿。不过,张跃莹不属这种情况。
张跃莹是高中毕业生,她家在长沙的境况似乎也不错。因为当初在农场时,她的衣着和用度都反映出这一点。不过下到生产队约一年,张跃莹就嫁在了自己插队的胡家(生产队)。张跃莹的丈夫我没有见过,但见过的知青伙伴对他丈夫的评价都不错。她丈夫也是个老高中毕业生,当时在大队当民办教师。
对张跃莹的婚事,张跃莹家里据说并不同意。她妈妈曾亲自从长沙来劝阻,也叫与张跃莹同过班的我们农场其他女知青帮忙劝。不过张跃莹的妈妈的劝阻极有分寸,并没有声张,当劝阻未成时,又坦然地接受了乡下女婿。过后,当张跃莹生孩子时,张跃莹的妈妈还多次从长沙赶来看望。当年从长沙到胡家湾(湾,当地话村之意)交通极不方便。不说从郴州到桂阳一天只有三几班车、从桂阳到樟市一天只有一班车,光胡家到最近的县级公路汽车停靠点,就要翻过两座比岳麓山高大的山岭,有十余里翻山坳过田垅的小路烂路要走。
大约是1978年,当时张跃莹的女儿刚出生不久,张跃莹的妈妈又准备到胡家来看望。听到自己丈母娘要来的消息,张跃莹的丈夫准备去山上打点心野味作招待。那时当地山上还偶有野猪、麂子等出没,胡家的人也喜欢打猎,而张跃莹的丈夫在村里还算一个不错的猎手。只是,当地人打猎不是在白天,而是在晚上。他们打猎是先想办法惊动猎物,然后用装了四五节电池的手电筒照住跑过来的猎物。据说被强光照住后,猎物就会站住,于是埋伏的人就是一枪。那天晚上张跃莹的丈夫与自己的好友来到山上,张跃莹的丈夫负责赶猎物出来,好友埋伏。但那好友在埋伏了一阵以后,却将黑暗中从树丛中走过来的张跃莹的丈夫当成了野猪,一铳放过去……。就这样,张跃莹在三十出头的年纪成了寡妇。
不久,知青大返城开始了。大家都以为张跃莹会离开胡家这块伤心地。已回城的知青朋友们也都劝她回长沙。但张跃莹没有。她仍留在胡家,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和两个稍大一点的儿子度日。先是胡家生产队让她顶替她丈夫当了民办教师,后来,县里又安排她进团结乡供销社做了职工,将她儿女们也转为了城镇户口。这时张跃莹虽然离开了胡家,却仍心系胡家。我们没有听说过她带自己的孩子回长沙、亲近长沙、接受长沙城市文化熏陶的事,却听说休息日她总是带孩子回胡家,使孩子们常绕于祖父母膝下,接受胡家的民风与文化。1995年纪念下乡30周年时我在团结乡张跃莹家见到过她的女儿,这个初中毕业后未考上高中在家待业的姑娘,是一个只会讲一口土话的典型乡下姑娘。
见她儿女们渐渐长大,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有的女知青伙伴曾试图为她在郴州条件不错的厂矿介绍合适的对象以便有个老伴。张跃莹谢绝了。她情愿在群山与田野怀抱着的团结乡过着清贫、安静、与世无争的生活。
现在,张跃莹的女儿也嫁了。大儿子则已为她生了个孙子。虽然两个儿子都只是在广东打工,但看来干得还不错。
2005年在长沙照顾卧床的母亲数月并最终送老母亲升仙之后,张跃莹又回到了团结乡。她虽然一个人住着半幢很大的房子,但在这人情味浓浓的乡下,她一点都不孤独。她每月领500多元的社保金,生活简单,但充实而愉快。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我认为,在我们农场来到桂阳乡下的一百多个知青中,张跃莹是一个心静如水的安安心心的扎根者。
2006年暑假,哥巴回桂阳时到团结看望张跃莹。要与她合影。她说老了,不想照相了。但哥巴的当地朋友趁大家不注意时按动了相机的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