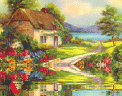。 陈乃广 2006。3。于长沙 。
公元1965年6月,(也就是长沙七千知青下放江永的第二年)江永县举办了首届农村俱乐部文艺汇演。 来自全县各区社的几十个业余文艺队伍带着自创的节目汇集到了小小的县城,数百名演员把江永县祁剧团的小剧场挤得满满的,热闹非凡,定睛一看,嘿嘿,清一色的长沙知青! 汇演进行了三天,各知青点的文艺积极分子除了在舞台上大显神通外,把个小小的县城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我感觉最大的收获是:享受了三天只有县三级扩干会议干部才能吃到的会议餐,让平时总是饥肠辘辘的肚子享了几天饱福。 汇演让江永县文化馆大开眼界,长沙来的这些伢妹子中竟然还有这么多的文艺人才,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于是县委当即决定,从这些人中间挑选一部分所谓文艺骨干,组成一只以农为主、以艺为辅的文艺轻骑队,为贫下中农服务,也为县委服务。
于是,在1966年元月,被挑选出来的27名长沙知青聚集到离县城八里地的一个叫接龙桥的地方,成立了江永县农艺队。 农艺队拥有两间茅草棚、三十亩水田、十多亩旱地,白天出工,晚上排练,从体力上来说比在生产队时还要辛苦,还更累。 但是二十几个活泼的年轻人在一起,是不会晓得苦和累的,不管是出工还是排练,大家都是劲头十足的,歌声笑声常陪伴着我们。
农艺队要为县里形形色色的各种会议演出,经常是通知一来,我们立即从水田里爬上来,水沟里洗净泥巴,晒谷坪里排练节目。 傍晚,会有一辆解放牌卡车将我们运到县城为会议演出。演完后便无人问津,我们摸着黑,拖着疲惫的脚步从县城走八里路回到自己的茅草棚,已是深更半夜了。 胡乱洗洗,钻进被窝,想着白天割的稻谷还浸在田里,明天要早起去拌禾……。
农艺队也常到边远山区为贫下中农演出,每到一处,见到那里的知青朋友,都感到格外亲切,他们夹坐在农民中间观看演出,还真分不出城里人、乡里人,看到此情景,我心中总是感到一种莫名的酸楚。
为了不再住茅草棚,我们开山炸石、挑砖运土、流血流汗的修建住宅,经过了将近一年的辛苦,我们终于告别了茅草棚,住进了一栋由我们自己盖建的两层楼的砖瓦房。
1966年春节,长沙市歌舞团到江永慰问演出,有人为农艺队拍下了这张唯一的集体照片,细看照片,唯独没有王伯明,说来也好像有一些巧合,那一次他不知因何故不在场。 一年后(文革中),王伯明在县城被人杀害……。
在这张发黄的照片中,已有向维嘉(后排左三)和杨剑英(前排左一)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另有何济清(三排右二)已因癌症于多年前去世;2006年*月,扬茨娜(前排左二)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文革期间,我因腰肌劳损回长治疗,紧接着因王伯明事件发生,大家也都陆续回长沙来了。 当时正赶上红一线文艺宣传队成立,农艺队中有一大半的人都参加了红一线文艺宣传队。
1968年8月,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语录发表后, 文革中返城的知青们又都陆续回到农村,农艺队的知青也不例外,
9月,一只由贫下中农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工作组以领导一切的身份十分威武的进驻农艺队,说我们农艺队是阶级敌人躲藏的窝子,一定要把隐藏的坏分子揪出来。 一时间,农艺队被一股高度紧张的空气笼罩着,每个人心中都诚惶诚恐,在那个年代,随便一句话就可以给你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任何辩解都是那么苍白无力,何况在农艺队,绝大多数人的家庭出身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在工作组进驻的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每天就是学习毛著、斗私批修、开会讨论、检举揭发,自己批斗自己……。 空气已经凝固了,呼吸好像要窒息,谁也不知他们到底想要怎样的结局。 最后,在工作组的刻意安排下,从队中揪出了五个“坏人”,有“炮打三红的现行反革命***”、有“打砸抢的坏头目***”、有“流氓阿飞***”、有“收听敌台里通外国的特务***”……,他们被公安部门带走,后来有一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蹲了五年监狱。
1969年初,成立了三年之久的江永县农艺队解散了,队员被分散到附近的生产队再次插队落户;几十亩田地被生产队收去;砖石结构的两层楼的房子成了养路工般的安乐窝。
整理于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