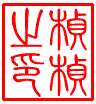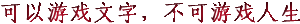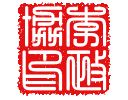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四)
1981年,一个喜讯从天而降,闵立宏那离别三十多年的母亲从台湾发来了寻亲信,在有关外事部门的帮助下她们联系上了。尽管这个喜讯来得太晚了,但终究还是来了!捧着母亲的来信闵立宏喜极而泣,“妈妈啊,亲爱的妈妈,我终于有妈妈了!三十多年了,我是怎样的想你呀!”从此,闵立宏生活中有了一件让她魂牵梦萦的事:盼母亲的来信,渴望见到母亲!
这一天终于来了!1989年6月的一天,在长沙的黄花机场,闵立宏和妈妈紧紧拥抱在一起,滚滚热泪洒落在彼此的身上。从记事以来,闵立宏第一次叫出了世界上最亲切的“妈妈”两字!妈妈已七十岁了,她皮肤白皙,气质高雅。她紧紧抓住女儿的手,细细端祥着女儿的脸。女儿的脸已经写满沧桑,乍一看比母亲还显苍老。
妈妈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夫婿为什么没来?夫婿是干什么工作的?家里生活过得好吗?
闵立宏最担心母亲问这件事,她不知道母亲会怎样看待她的选择。除了在年龄上给了母亲一个善意的谎言外,其他情况她都如实说了。母亲仔细地听着女儿的讲述,末了,她说,你受苦了。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你还能站住,同时,还做了不少造福人间的工作,真了不起!感谢神,祝福你!你夫婿对你很不错,很照顾体贴就够了,不要人比人,知足常乐才是福呢。
母亲的安慰和称赞出乎女儿的意料,闵立宏感动得又流下了热泪。似乎几十年来所受的苦都化为了甘露,她心中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和敬佩。母亲时刻关注着女儿,连女儿打个喷嚏她都急忙问:“家家,你受凉了吗?”
闵立宏原名闵家珍。文革中,叔叔为她改名立宏,希望她立下宏志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家珍这个名是父母请菩萨取的,这是个富贵的名字,意即家里的珍珠。在长沙与母亲相聚的几天她深深沉浸在母爱之中。
无奈的是,当时正临近初中毕业生的中专预选关键时刻,作为班主任又轻易不请假的闵立宏,为了母女重逢向学校请了十天假。
得知这一情况后,第六天,母亲便对女儿说:“家家,你教的是毕业班,学生离不开你,如果你工作没搞好,我心也不安。”闵立宏真没想到离假期还有几天,母亲便要她离开。四十多年的分离才相见五天,母女怎忍心再分离?这时,她抬头望了一下母亲,只见她眼眶里噙满了泪水,闵立宏禁不住潸然泪下。她们沉默着都说不出话来,彼此感到了一种骨肉分离的揪心的痛。
与母亲相聚的第六天,闵立宏便返回了沅江。
闵立宏回到黄茅洲后,家也没回就直奔学校。她忘不了临行时学生哭着对她说:“
还没走到校门口她便碰到班上的两个女同学。两个女孩高兴得跳了起来,一个抢上来帮老师提行李,另一个一溜烟跑进了学校。等闵立宏走上三楼时,只见楼梯两边站满了学生,掌声、鞭炮声炸响,学生们夹道迎接亲爱的老师!走进她任教的五十七班教室,直扑眼帘的是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的“热烈欢迎
刚经历了与母亲痛苦的别离,现在又溶进了这热烈诚挚的师生情谊里,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任由泪水簌簌地流……此时此刻,她才深刻体会到母亲话语的份量,感受到母亲心怀的博大。
她写下《我最尊敬的人》一文,表达了她对母亲的几十年的思念与敬仰。她将文章读给学生们听。她由衷地说:“我时时不能忘记,为了孩子们,我的母亲作出了怎样的牺牲,母亲的爱是何等的伟大。”
从两岁到五十八岁,整整五十六年,闵立宏仅仅享受了六天的母爱。她告诉我,自那次和母亲见面后,母亲多次在信中表示,她很想到乡下来看看。但想到女儿任教的是毕业班,就打消了念头,这位曾经当过教师的母亲深知教师责任的重大。
不知道她们母女何时才能再相见。
(五)
告别立宏姐之前,我和她一起去看望了她的几个儿子。
在老屋的旧址上,贵安和铁军各有一套房。当时正逢他们收割第一季荨麻。贵安种了四亩,铁军本没有田土,是贵安给了他二亩地。他们都请了帮工。老三贵财也来帮忙。他住在别处,有一栋很大的新宅。他在做建材生意,是目前四兄弟中最发达的。
立宏姐一到贵安家就做饭、洗衣,忙个不停。
房前五十来米开外是麻田。烈日下,收麻的人竹笠上搭着毛巾,腰上围着块布,弯着腰,右手折断麻杆,手指迅速带下麻皮递到左手上。直到左手握不住麻皮就将它扭成一股放在地下。青青的麻皮在他们的手中右一捺、左一撇,动作十分轻快优美!我眼前幻化出一幅库尔贝的油画“收割季节”……一堆堆剥下来的麻皮被送到屋后的坪里。这里是下道工序:打麻,即把剥下的麻皮除掉皮,留下麻纤维。贵安、贵财,贵安的爱人都坐在打麻机上,手不停脚不住地剥打着麻皮。
吃过中饭,我们到铁军家休息。他那三室一厅的房子是四年前新建的。客厅约三十个平方,摆放着二十九寸的大彩电、音响、木沙发,有着小康家庭的景致。立宏姐说,这三四年来铁军两口子外出打工,还清了建屋的债,置了这点家业。现在儿媳还在外地打工。
贵安已在大路边买了块地准备建新宅,那地方方便运输,有利于他做的煤炭生意。他告诉我:“还是妈妈要我搞煤炭生意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铁军长得象妈妈,比哥哥们高大。他不善言谈。说起母亲,他只讲了一句:“我的妈妈这辈子付出太多,得到的太少,将来我要在沅江买套房子让她过好点。”
作回长沙的准备时我提出想看立宏姐母亲的来信。立宏姐忙拿出钥匙,从柜中取出订成一册的信给我,要我带回家看,以后再还给她。
我们等着已联系好的去黄茅洲的面的。
这时,一个邮递员走了进来。他手拿一包裹,问道:“有不有叫闵家珍的?”立宏姐忙答应:“有咧!”我接过包裹一看,是台湾寄来的。这个邮件三个面都被盖上“查无此人,原件退回”的邮章。邮递员说,好象记得学校里有个姓闵的人,还是过来看看。立宏姐一边说谢谢一边接过邮件。看着邮件,她高兴地说:“这是我妈妈的字!”打开纸袋,里面是一本精装的闵氏家谱。拿出家谱,她又把手伸进纸袋,却一脸的失望:“怎么没有信?”立宏姐翻开家谱,见到了父亲和叔父的照片。家谱表中,闵家珍和陈学纯的名字并列其中。这家谱的第一页左下边有手书的069闵家珍 陈学纯字样。家谱沉甸甸的,捧在手中很有份量。然而,我感到,立宏姐的心头更沉。
她的母亲己经好久没有来信了,她写给母亲的信都没有回音,而远在台湾、美国的弟妹们又一直没来得及联系上。不知道八十多岁的母亲现在怎么样了,她盼望着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她的母亲。
我不知道立宏姐的母亲是否还健在,但我知道她老人家可以安心了。她的女儿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就没有再过不去的沟沟坎坎。她的生命之舟已经越过了急流险滩,正带领着儿孙们驶向宽阔的江面,驶向美好的明天。
(六)
我回到长沙不久,就收到贵安的信,在信中他深情地写道:“蒋姨,我一直有一种想写文章的冲动,就是想写一篇‘母亲的回忆’,回忆妈妈经受的艰难困苦,她那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的事迹。但由于我没能考上大学,学业无成,后又忙于生计,自卑感和时间的紧张我始终无法拿起那沉重的笔。听说您要为我妈妈写篇文章,我们兄弟非常高兴!蒋姨,您了却了我埋藏在心中多年的心愿。太谢谢您啦!”
我为他的信所感动。我想,能尊敬一个善良的人,有感恩之心的人,他本身也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于是,我写了立宏姐。写的过程中,我总想起了“毛蜡烛”。
“毛蜡烛”是一种盖茅屋的材料。是几个世纪以来洞庭湖区穷苦百姓的一大发明。
人们将湖边自生自长的芦苇砍下来,将芦苇杆修理整齐后,紧紧缠绕上用稻草搓成的绳子,便做成了一支支的毛蜡烛。然后,一支支毛蜡烛紧紧密密地排放到用木材和楠竹搭起的屋架间。最后,里里外外糊上掺和着牛粪的泥浆,便筑成了光溜别致的新屋的墙。这墙冬暖夏凉,能遮风挡雨。和所有农民一样,我们当年的知青屋便是用稻草加毛蜡烛盖的。
我总觉得立宏姐就像毛蜡烛,身单力薄,默默无闻,用她一生那真诚无私的爱为一个破碎的家,为几个孩子飘泊的心撑起了一片天。而那位爱护立宏姐的农民陈学纯和他的三个孩子又何尝不是她的毛蜡烛呢?
爱,是没有标准的;真诚的爱,永远无法衡量。
在本文搁笔之际,我接到立宏姐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
电话那头的声音非常响亮,我知道,立宏姐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
拿着话筒,四十多年的岁月在我心中一晃而过。
明 瑞
2007年2月6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