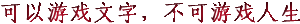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三)
再次见到她是在五年后了,我又一次由女儿陪同到了沅江,立宏姐的体态有些发福,脸色红润,精神显得好多了,只是背稍有点弯。一进她的家,就感觉亮堂了许多:地面铺上了白色的瓷砖,墙壁刷白了,原放藤椅的地方摆上了一张简式长木沙发。有了一台老式的电视机,电话也装上了。
陈爹不在了!他于2003年因脑溢血去世了。睹物思人,看到这张木沙发我便想起了那张藤椅,想起陈爹端坐在上面让我拍照,笑眯眯地讲述他和闵立宏的故事。立宏姐说,家里没有陈爹太寂寞了,她一个人不想住。上初中的孙儿陈彬和上小学的孙女陈思思陪她住在这里。休息日儿子便把祖孙仨接回家。
每天清晨五点半立宏姐就起床了。她很快做好早饭,照顾两个孙儿吃过饭去上学。我也跟着过了几天早起早睡的日子。在她家的几天,不管是在外出的路上,或是她做家务的空隙,立宏姐便会断断续续给我讲述她和陈爹的故事。
,1971年后,闵立宏那个小组的知青,招工的招工,回城的回城,最后只剩下了她一个人。每次招工贫下中农都推荐了她,却都因“台属”问题被刷名。
闵立宏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虔诚地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什么累活苦活都干,连男劳力翻凼子这种重活她也干。队里的双抢任务很重,因抢时间半晚就要起床出工。知青组有闹钟,社员希望他们能叫大家起床。闵立宏主动承担了此事,每天半晚她便跑遍全队挨家挨户地叫社员起床出工。
农民注重实事求是,他们看重闵立宏,把她送到大队小学当了民办教师。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这是知青诗人郭路生那首著名的《相信未来》。诗所表达的悲怆和忧伤的乐观旷达使闵立宏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她由衷地喜欢这首诗,好象这首诗是专为她写的。寂寞的时候,她常常独自呤颂着。
也许是种命定的缘分,知青屋最近的邻居就是陈学纯家,陈学纯平时就很关心知青,在闵立宏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他常让八岁的儿子贵安过来陪伴她。贵安精精瘦瘦,机灵乖巧,他和弟弟贵财特别亲闵立宏,闵立宏也十分同情他们。
贵安六岁那年,生母去世。紧接着,两个妹妹也死了。六个月时间,家中连死了三个人。陈学纯被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弄得焦头烂额,就象天塌了一样悲伤。他们搬离了悲惨的老家,到塞阳运河边搭起了一座简陋的茅屋。同年,即1968年12月,闵立宏和十个知青下到了他们生产队,房子就建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陈学纯忙于大队的工作经常不在家,大儿子要出工,贵安和五岁的弟弟贵财常常没饭吃,既没人煮,也没米煮。他们就常往知青屋里跑。渴了,他们能喝上开水;饿了,准能吃上一顿饱饭。特别让他们高兴的是,在这里能吃到白米饭,在他们家只有过春节才有白米饭吃,这让他们常有过年的兴奋。
没娘的孩子衣裳褴褛,贵安几兄弟一年四季没穿过一双完整的鞋子,捡到一只穿一只,象济公和尚一样。冬天他们根本无法洗澡,平时做饭烧水都没柴,要想烧火取暖洗澡是不可能的。到了冬天,手脚都被冻得开裂,要到第二年的阳春三月才能好起来。每次到了知青屋,闵立宏总是帮他们洗干净伤口,抹上膏药。
成年后的贵安常说起小时的一件事,说起他最难忘的一天。“那是一个冬日里难得的艳阳天,大地被晒得暖洋洋的,四处蒸腾着热气。妈妈烧了两大锅水,把我和弟弟泡在大木盆里,给我们痛痛快快洗了个澡。我看到弟弟脸蛋红彤彤的,头发闪闪发光,眼睛乌黑发亮,一脸的惬意。我更是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开心!洗完澡,妈妈拿出自己的衣服让我们暂时裹上,把我们脏得油黑的衣裤全洗了。那叫什么裤啊?裤裆都没有,全裂成了一片片的破布条!她费了不少工夫才将这些衣裤缝补好。”
这时的闵立宏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疼爱她的人们有的为她出主意,有的为她介绍对象。她都拒绝了。东红学校的
“难怪陈爹说是你追他,他家那么穷,你不是自找苦吃吗?”我脱口而出。
“我觉得他的命运也值得同情,而且他为人正直,忠厚老实,能心疼我。和他在一起有安全感。当时我只提了一个要求,只不出去借米”。
就在这时,闵立宏接到了长沙发来的电报,称奶奶病重要她速归。回到长沙后才知道,亲人们知道了她和陈学纯的事,极力反对,认为她是往火坑里跳。闵立宏无法说服他们,他们也没能阻止她。
闵立宏和陈学纯的事在黄茅州区成了爆炸式的新闻,一时间,政治压力和流言蜚语纷至沓来。有人认为,黑七类狗崽子闵立宏腐蚀贫下中农干部,是破坏党的阶级路线;更多的人为闵立宏担心:找亠个又老又穷还拖着三个孩子的农民结婚不是自讨苦吃吗?一个城里来的女学生能一辈子吃这种苦吗?
1971年12月初四,他们就在陈学纯破旧的茅草屋里结婚了。当时她二十五岁,他四十二岁。茅草屋里仅有三张土砖架的平头床,外加一个老式两门柜。他们婚礼的见证人就是三个儿子:十八岁的陈贵芳、九岁的陈贵安、八岁的陈贵财。三个孩子欢天喜地,在他们心中,闵立宏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他们的潮湿阴暗的茅草房。
婚后,他们俩人都受到了处分,陈学纯由大队贫协主席降到了生产队长。闵立宏也被解除了教师工作。
闵立宏成了道道地地的农村妇女。第二年,她怀上了儿子铁军,家里仍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米桶空空荡荡,菜不是剁辣椒就是米汤加盐,根本不可能给她弄点什么补补身体,而家务事地里的活她照样做。从小就瘦弱的她,体质本就差,这一来整整七个月,强烈的妊娠反应折磨着她,她的体重由原来的一百二十斤降到七十五斤!十月,她生下了铁军。骨瘦如柴的闵立宏没有奶喂儿子,牛奶没钱买,五角钱一包的奶糕也保不住天天有吃。从娘肚里起,铁军便严重缺乏营养,他的体质一直不好。
1973年,大队缺少小学教师,闵立宏又被请上了讲台。尽管劳动强度有所减轻,但压在她肩头的担子更重了。铁军要哺育,贵安和贵财都上学了,每期的学费是沉重的负担。艰苦劳累的生活让闵立宏病痛缠身,她患上了阑尾炎、结肠炎、支气管扩张(吐血)、脊椎炎、子宫肌瘤(手术摘除)等病。一个星期天,闵立宏忽然吐了口血,她没放在心上,下午仍到学校去开周前会,会后大口吐起血来。半夜里,校领导,老师们将她送到子母城医院,打针、服药,但收效不大。后来是两个钟头吐血一次,反复发作。为了不耽误上课,第二天,她又按时站到了讲台上。上完一节课,她又吐血了,她被扶到床上躺了下来。学生们这才知道,
一个学生在作文中写道:“老师,您为了我们劳累奔波,仿佛不知道休息,只知道工作。您多次病倒,又多次拖着病体给我们上课。备课阅卷、深夜家访,又有多少次苦口婆心地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您可曾知道您的眼睛一天天陷下去,您脸上的皱纹一天比一天深,头上的银丝一天比一天多。”学生的理解与尊重是强心针,站在讲台上的闵立宏总是一张笑脸精神抖擞地讲着课。每上完一天课回到家,她总象个打了胜仗的战土那般为自己庆幸,瘦削的脸庞挂着舒心的微笑。看到她的笑脸,父亲和儿子们既高兴又心痛。每当家里打牙祭——吃白米饭时,总要省下一碗给她回家吃。早出晚归的闵立宏见到这碗饭,望着几个“吃长饭”的儿子怎么也不肯动筷子。她推说在学校已吃饱了。那段时间他们常到镇上排队买米豆腐当饭吃。她哪有中饭可带?早餐吃的是米豆腐,能饱到哪一时?儿子们非要妈妈吃,妈妈却将碗往儿子面前推。推来推去,谁也舍不得吃这碗饭,最后这碗米饭馊了。白米饭是稀罕物,可在他们家却总有白米饭发馊的故事。
闵立宏一直为一家人的鞋发愁。天渐渐凉了,还筹不起买鞋的钱。她决心自己做。她仔细向别人请教了做鞋的方法,抓紧休息日和晚上的时间干了起来。裱衬壳得赶太阳,要将破衣旧布洗干净整理好,再用浆糊一层层裱在板子上晒干。衬壳赶出来了,接着是纳鞋底。她不熟悉走针用力,针鼻常常倒扎进手指中,手掌上满是被麻线勒的条痕……整整一个秋天,她赶完了前面的工,只剩下上鞋面了。吃了晚饭,点上油灯,坐在床上,用被子盖上脚,她穿针引线赶着活计。春节快到了。一天,吃过晚饭,闵立宏笑嘻嘻地对全家人说:“你们猜猜今天会有什么喜事?”见他们楞在那里,她又说:“你们快洗脚吧,是穿新鞋!”闵立宏转身拿来一捆新鞋,分给每人一双。“我穿新鞋了!我有鞋穿了!”儿子们高兴得蹦跳。他们还是第一次尝到穿新鞋的滋味呢!新鞋是青布做的,滚着白布边。在他们的眼里,这是世界上最漂亮最舒服的鞋!闵立宏脸上堆满了舒畅的笑。她说自己又学会了一门手艺。贵安说:“回想起这件事,想起妈妈那双手,现在心里还痛呢!”
湖区的冬天,北风肆无忌惮地吼叫,夜晚显得特别长,特别叫人难捱,烤火是奢望,唯一可做的是钻被窝,到睡梦中去享受你想要的东西。往常,他们家很早就熄了灯。自从有了妈妈,孩子们也有了“夜生活”。闵立宏不知从哪里弄来《西游记》、《三国演义》、《笑话集》等书。到了晚上,大家都窝在被子里,不是躺下,而是坐着。闵立宏拥着被子,就着煤油灯光给他们讲起故事来。她平时讲话总是和颜悦色,不急不慢,语调平缓,毫不张扬,讲起故事来却完全进入了角色。她说起孙悟空语调变得响亮明快;学起猪八戒变成了油腔滑调;逢到沙和尚,语气变得厚重朴实;讲到唐僧,满腔慈悲语言庄重。父亲张开嘴听得入迷,儿子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妈妈,完全被带入了那引人入胜的神话世界。房间里时而鸦雀无声,时而爆发出拍击床板的啪啪声,时而充满了开怀的欢笑。
回忆这两年的生活,儿子贵安感叹地说:“七三年到七四年是我们家生活最苦的两年,也是我们最快乐最难忘的两年。”
闵立宏有几年没回长沙了,她想念奶奶和叔叔。陈学纯本想陪她去,又实在拿不出那些路费。让闵立宏一人去,看着她那虚弱的身体,他又放心不下。考虑再三,觉得让贵安跟着去最合适。他只需买半票,也懂事了,路上可以帮妈妈照应一下。贵安听到这个决定,激动得一夜没睡着。动身前,全家人足足张罗了半晚,总算准备好了行装:一担箩筐,小铁军坐在一只箩筐里,另一只箩筐放的是礼物:几斤芝麻黄豆,还有点盐菜,外加几蔸白菜芽白。这些都是自家产的,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家里最好的东西。第二天清早,陈学纯挑着箩筐将仨娘崽送上了去长沙的轮船。
坐了整整一天船了,贵安一直眼巴巴地盯着窗外,只盼快点见到长沙城。直到船外一片漆黑长沙城还看不到影子。船里鼾声渐起,人们纷纷入睡。贵安坐在船板上,头靠着闵立宏的座位也来了瞌睡。铁军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突然“咚”的一声,贵安被惊醒了。睁眼一看,弟弟铁军掉在地板上,正哇哇大哭。闵立宏双眼紧闭,牙关紧咬,不省人事。他吓得哭喊着妈妈。乘客们被惊醒了。一位老大爷连忙帮闵立宏拉筋,掐人中。几位乘客拿来开水和食品。铁军见到其中的蛋糕止住了哭,扑上去抓住一块直往口里塞。担心他噎着,贵安赶忙端起开水喂他,将蛋糕撕开送到他嘴里。他狼吞虎噎竟三口吞下一块蛋糕,一连吃了八个外加一碗开水!他才一岁呀!要知道,这是他从娘胎里开始第一次吃上了一顿饱饭!在好心的乘客们的询问下,贵安才想起妈妈从上船到现在整整十几个小时了还没吃过一点东西。白天仅买了盆饭给他吃了,她自己一口也没吃。她是给饿晕的!
闵立宏终于苏醒过来了,她瘦削蜡黄的脸上显得那样疲惫不堪。看着周围的人,她显得十分平静,似乎对这一切都习以为常了。虚弱的她常支撑不住自己,曾多次晕倒。她谢过大家,就象一切不曾发生过似的,抱起铁军,帮孩子擦擦脸,哄他睡着了。凌晨,船终于到长沙了。闵立宏挑起担子一步一挪地朝她的老奶奶家中走去。
闵立宏奶奶家在长沙市左局街,那是一条热闹的老街。贵安好奇地东瞧瞧,西看看,他发现,人们都以异样的目光看他们,有的人还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他不解地抬头看看妈妈,妈妈拉起他的手,微笑着告诉他,就要到曾奶奶家了。小贵安啊,你又怎么知道,这里的人们熟悉的那个朝气蓬勃的女学生,竟变成了这位浑身乡土味,用箩筐挑着孩子的你的妈妈!人们无法理解你的妈妈呀。
我禁不住问立宏姐:“你后悔过你的选择吗?”
她摇摇头说,“我没有过后悔的念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任何一对夫妻都存在,只不过我们比较特殊罢了,如年龄的差异、文化程度的悬殊、兴趣爱好的不同。前些年我们很少走在一起,平时除了生活话题外很少有共同语言。看电视他就看新闻,电视里的对白、普通话他很难听懂,少不了常要我当翻译。对于屏幕型象他只看毛泽东,其他内容他一概不感兴趣。一般夫妻该有的幸福我可能没有,但一般夫妻没有的幸福我也许得到了。”
立宏姐讲起了陈爹对她的关怀备至,至今仍感到十分温馨。
她调到子母城学校后,离家较远,不能常回家。陈学纯在家喂了二只鸡。鸡下了蛋自己一个也舍不得吃全积下来,往返十几里路送到学校给她吃。他会算准日子将柴、米、青菜及时送到学校。冬天,闵立宏特别怕冷。以前没火烤她只能坐在被子里备课,很不舒服,而且墨水把被子弄脏了都无法洗干净。八十年代以来,湖区的农民普遍烧起了煤炭,冬天也用上了烤火炉。陈爹专为闵立宏做了个木火桶。每天他都生好煤炉放在火桶里,上面盖上被子。她下课回到家,坐到这暖烘烘的桶上,舒舒服服地看作业备课。
晚年的陈爹在家做家务,种种菜。不再愁白米饭,蔬菜基本自给自足,陈爹很满足,吃不吃晕菜无所谓。不过,一想到瘦弱的妻子,他有时也会去肉铺,买两块钱肉回家。那天,他过细地把肉切碎做成汤端起锅连汤带肉都倒进一个菜碗,然后往菜碗里盖上饭。闵立宏下课回家吃饭。他将菜碗摆在她面前,自己端起饭碗吃起来。闵立宏正奇怪怎么给她菜碗吃饭,扒了几口才发现“秘密”。她一定要俩人分吃这碗饭。他硬是不肯,将碗直往她面前推。“你不吃我就不吃!”闵立宏气恼了。“我早己吃过了,吃不下了,你别浪费!”陈爹硬梆梆地说。他们吵架般吃完这餐饭。家里只要吃点晕菜象这种“吵架” 是常事。
陈爹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他患了因脑血管短暂缺血引起的眩晕病。一发病就呕吐、晕倒。在他患病的六年中,闵立宏看了很多有关心脑血管疾病的书,收集、剪贴了许多有关的医药资料,懂得了一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病症用药常识。她几乎成了一位颇有经验的家庭医生。陈爹舍不得上医院看病,闵立宏只能瞒着买药回家给他吃。有时候闵立宏硬拉着他到沅江市或其它地方的医院去治病。而闵立宏一有不舒服,陈爹便催促她去看病,把药煎好送到她手里。什么事都不让她做。直到陈学纯七十五岁去世,闵立宏和陈学纯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三十二年。三十二年中从未吵过架,更没为钱的事吵过嘴。
1975年,沅江县实行农田机械化建设,要求农民的住房成片成线。陈学纯家在拆迁之列。他们家也实在该砌新房了,几兄弟都长大了,一家人挤在一间房里太不方便了。可是,砌新房哪里有材料?这时,有关领导将当年知青空着的住房安排给了闵立宏。真是雪中送炭!知青屋的材料加上自家屋拆下的些微可用的材料,他们勉强搭起了三间茅屋。知青剩下的一张床和柜成了他们家最好的家俱。
这时,贵安考取了高中。每到开学时,学费便成了最大的难题。五十元左右的学费对于这个年收入近乎零的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那时闵立宏当教师的年收入是六千工分,家中唯一的现金收入是她当民办教师的每月五元钱工资。她尽可能积攒下每一分钱。贵安读高三时,家里连这每月的五元钱都无法积存下来。开学几天了,贵安还没有钱交学费。他对父亲说:“每次都是妈妈给的学费,你也帮我交一回吧!”父亲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没有办法,只有工分没有钱!”第二天,垂头丧气的贵安背着空书包正准备往学校去时,妈妈叫住他:“安伢子,学费有了,你拿着!”真是喜出望外,贵安接过钱奔跑着去学校。后来他才知道,过春节妈妈回长沙时,叔外公给了她三十元钱和五十斤粮票,要她给家里买点粮食。妈妈一直不敢动用这笔钱。为了他,现在全家人又要勒紧腰带了。
眨眼工夫,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到了,贵安又要交学费了。家里再也拿不出钱了。他想,这次只怕真的读不成书了。几乎绝望的他怎么也没料到,开学没几天,妈妈将五十元钱塞到了他的手中,要他去交学费。贵安仿佛做梦一般,不知道钱是从哪里变出来的。直到晚上回到家里,他才发现,家中那张唯一的好床――妈妈的知青床不见了。摆在那里的是用土砖架的床。他问妈妈是怎么回事,妈妈只是笑着反问:“这张床不好吗?”他立即明白了,妈妈把床卖了,床变成了学费!霎时,贵安眼泪夺框而出!
贵安在日记中写道:“这么好的娘,在全中国恐怕全世界也不多见,偏偏让我们碰上了。我常想,我的祖上不知积了什么德,保佑我们遇上了这么好的妈妈。妈妈啊,您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美德于一身,您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在春回地暖的1979年,闵立宏头上的“台属”帽子消失了。她被转为城镇户口,调到沅江县子母城中学,成为正式的拿国家工资的教师。贵芳、贵安、贵才三人都能出工干活了,家里的生活渐渐有了改善。这时,儿子们的婚姻大事又成了她最操心的事。当时的农村仍然贫困,娶一个媳妇相当困难。订婚时,男方要给女方送三大件聘礼:手表、单车、缝纫机。还要给女方及其亲戚送现金、酒、肉、布等,这得花上二千多元。结婚时还得花上二千元左右。为筹备贵安和贵才的婚事,她先后向十五个人借过钱。借款最高的七百元,最低的一百元。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靠的还是闵立宏的工资。闵立宏当民办教师时每月工资仅五元,转正后二十九元五毛,(以后慢慢增加,到退休时四百多元)夫妻俩千辛万苦,从牙缝里省出一分一厘钱,还清了所有的欠债。在闵立宏的操持下,儿子们都有了幸福的小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