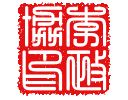农场生活点滴
谭世通
1965年9月9日,我从长沙上山下乡来到桂阳县樟市人民公社第二农场。说农场,实际上就是一幢古IEt的大屋和几处完全没有水源、布满杂竹和荆棘的几百亩山坡荒地。下来的头一年,知青们每人领取二百二十块钱的安置费,享受国家一年的定量粮食供应。一年以后就靠我们的双手在这片荒山坡上创造财富,自力更生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两个字:苦干。
虽然下农村之前我也做好了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但是,樟市二农场的劳动之累、生活之苦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每天清早,开工的哨声撕破黎明的帷幕。我睁开惺忪的睡眼,挑起担子往地里赶。当太阳被西山吞没、百鸟归巢时,每人还要收捡一担竹根、树桩回去给伙房做柴烧。又累又饿的我,一百斤不到的稚嫩肌体,挑着一百几十斤的沉重担子,一摇一晃地走几里崎岖的山路,一路上,腹中咕噜,腰往下沉,腿如拖铅。遇上雨天,雨水和汗水浊流如线,脸上形成一道道沟壑,泥浆和着草根粘附在脚上,叫你举步维艰。
劳动最苦的一页,恐怕是我以手捧大粪的一场闹剧了。那是1965年抢种冬小麦的时候,由于省委王书记的关照,免费拨了县城的一个公共厕所给我们农场掏粪,做小麦的底肥。这样,农场每天都派三个人进城去拖大粪。那天派我与另外两个同学一早就拖着板车上路了。
从樟市公社到县城二十四华里是简易公路,那路道狭窄弯曲坑洼,又要翻山越岭,随时有危险迎接我们。果不出所料,当我们拖着沉重的运粪车返回途中,在一处正要下坡的地段,一辆开足马力冲坡的汽车迎面闯来。我们拖粪的三人一个十九岁,我十七岁,另一个十五岁,由于体力不足,慌忙避让时板车失控,冲到路边的一个土堆上, “嘭”的一声,车上的大木桶连同六担粘稠的大粪全倒在了公路上。我们急坏了。怎样才能将流满一地的粪便重新弄回桶中?我们没带工具,这山坳里又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大粪臭烘烘的,更重要的是农场那贫瘠的红土山地等着用。怎么办?三人商量,我们不是说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吗?那还怕什么脏呢?于是我们不顾一切,立即用手捧大粪。终于,大粪全被我们用手捧到了大粪桶中,回到农场装到小粪桶中还有四担半。
见我们没有拖足六担粪回来,生产委员还批评我们偷懒。我们也不解释,因为这事本来是我们无能,失职了。一想起那番情景,至今还想作呕。
劳动的时间长、强度大,而伙食如何呢?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月九元钱,也就是每人每餐不到一角钱的伙食费。三餐开饭八个人一“桌”,每人一钵不到四两 米的蒸饭。桌中摆-Ib钵冬瓜或县茄子、剪卜 轴陈稆 足,就是没有飘上几个油花。有时连小菜也没有,仅摆
着一钵清澈见底的辣椒汤。将汤分到各人的饭钵中泡 饭,顺水淘沙填人肚中。饭量本来不足,肚内又少有油 脂,刚放下碗,转出食堂,饥饿就扑袭过来。
何时才能吃一顿饱饭?我们盼望已久的1969年元旦 来了。因为场长早就宣扬,农场养了两只猪,元旦要杀 头猪打牙祭。元旦晚上,食堂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 很久没有这么高兴过了。从公社借来的煤气灯把食堂照 得如同白昼。大家以“生产队”为单位(农场那时把全体 知识青年分为六个生产队),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敞 开肚皮享受那久违了的肉食。
为了准备这顿丰盛的晚餐,我们的大师朱胖子将同学们较好的脸盆全都收上来做了菜盆。红烧肉、粉丝 肉汤都是用脸盆来装的。这样的大会餐真叫过瘾。久未 拈过油水的肠胃,今天可谓是久旱逢甘雨。元旦这天不 但吃得好,也玩得很开心,白天看了广州军区战士歌舞 团的游行和精彩表演,晚上又到樟市圩看大型音乐舞蹈 史诗《东方红》的电影。
然而,真是乐极生悲。过量的贪馋,给自己带来了不 幸。那一夜,大家都没睡好,厕所却热闹起来,我也跑 了好几趟厕所,每次急急忙忙跨上茅坑还没有蹲稳,稀 求就从肛门喷射而出。争占茅坑的场面,成了大家互相 邸揄的素材。我吸收这次暴食的深亥4教育,一个月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