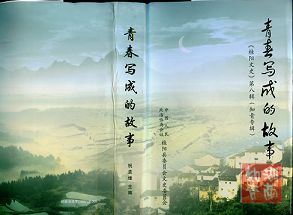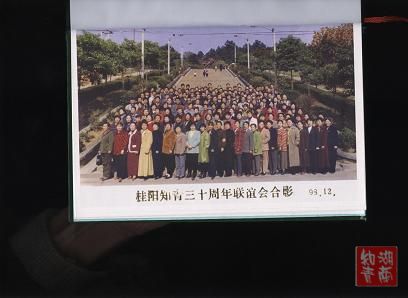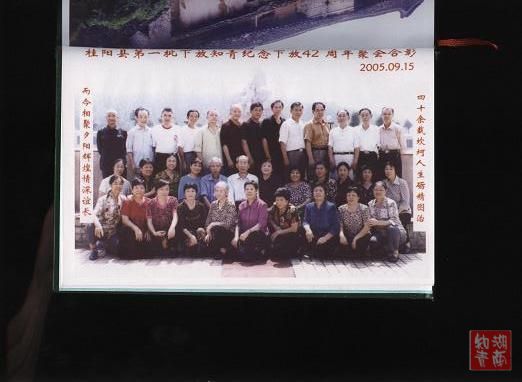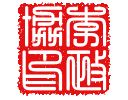在岭下,我接触到的不再是以某种虚假理论为蓝本,经过精心编造的那些书本、电影、报纸上的虚幻的农民。我接触到的是一个个真实的农民。同时我接触到的农民的生活,也是真实的农民的真实生活,而不是那些编造出来的农民虚假的生活。在岭下的乡亲们中,三爹与他两个兄弟的往事,大概可以算得上是过去农村、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三爹和他两个兄弟的生活经历,就成了我认识真实的中国农民与农村过往生活的标本。
三爹的大名叫何修元,是生产队会计何嗣平的父亲,他生于宣统年间,虽然我到岭下生产队时他只有六十出头,但却是岭下村辈分最高、年纪最大的老人。
三爹没有上过学。他说在他三兄弟中,他和他大哥修觉都没有读过书,只有他老二修麟读过多年私塾。
“我老二从小身体不好,所以我父母想让他读书找出路。但他不中用,没读出个名堂来。”三爹这样评论自己的二哥。
三爹与他的两个兄弟虽然由同一父母所生,但土地改革时三爹的“阶级”却比他两个兄弟都“高”得多。
三爹的大哥修觉死于解放前的“民国三十五年”。由于他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因此他儿子“马拐”的成分就理所当然地是雇农,属农村中响当当的无产阶级。
三爹的二哥修麟,拥有近二亩由父母传下来的田土。但是修麟儿女多,不得不租了些地种,而且家庭生活贫困。因此,修麟家的成分是贫农。
三爹呢,土改前他已拥有十几亩田(一九六八年我下到岭下生产队时,全生产队也只有四十二亩田)、几片产量可观的油茶林和一处老屋、一幢新屋,还同时养着一大一小两个老婆。论家产,三爹虽然与土改时被划为地主,“社教”时定为富农的何典金家不相上下,但他却只被划为富裕中农。
俗话说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当夏夜坐在村口乘凉时,三爹总爱对我讲他过去的一些往事。由于三爹不是地主富农,我不用担心他造谣、“放毒”,所以对他讲的那些过去的往事,我既放心地听、同时也相信它们的真实性。
与他大哥修觉一样,三爹年轻时也当过兵。“当时我们就驻扎在你们长沙”。因为我来自长沙,所以三爹特意强调他也曾到过那里。不过,三爹在军队中没有干多久就开小差当了逃兵。他说他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逃出兵营的。躲过搜捕以后,他长沙、湘潭、衡山、衡阳、祁阳、归阳(镇),一路历尽甘辛,靠步行回到了八百多里外的岭下家中。
三爹的父母,想必也是贫穷的农民。因为据三爹说,他们三兄弟分家时,每人只分到一亩七分田土(我到岭下生产队时,生产队人均田土是一亩四分。三爹兄弟当年每人分得的田土多于几十年后岭下村的人均田土数),可见三爹的父母总共只拥有五亩多田土。
由于只从父母那里分到一亩七分田土,所以最初,三爹的家境并不好。一亩七分田土的出产,一个人糊口大概够了,但要养老婆孩子则显然不行。同时,一亩七分田土的农活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于是在侍弄这一点点田土的同时,三爹也外出当脚夫。沿着那弯弯曲曲的连接湘南与粤北的石板古道,三爹与其他脚夫伙伴为商人将茶油桐油等湘南土产挑到广东乐昌,然后再从乐昌挑海盐回来。
从桂阳州(老辈人仍按古时的叫法称桂阳县为桂阳州)到乐昌来回要走好些天。白天,脚夫们挑着百斤重担,翻山坳、过田垅地赶上百十里路,辛苦自然不在话下,不过夜晚,当他们到达投宿的乡镇小伙铺时,也还是能够好好休息一下。那些乡镇小伙铺不但供应热菜热饭热汤,还有热水给脚夫们烫脚。伙铺的老板对脚夫们十分亲切,老板娘还常与脚夫们“打情骂俏”。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赢得脚夫们的好感,下次再来住他们的店。
三爹说,那些乡镇小伙铺不单只向过往旅客提供食宿,也提供一些其他隐秘服务。例如,只要你肯出钱,伙铺的女用人会为你洗脚、甚至陪你上床。挣的虽然是辛苦钱,但仍有脚夫经不起伙铺里的“女用人”甚至老板娘本人的引诱。结果,“肩膀上压出槽,抵不了床板摇”,辛辛苦苦肩上压担子压出槽来才挣到的几个钱,随着床板吱吱一摇,就从自己口袋流入了别人荷包。
三爹那时虽然年轻,但并不风流。不过最主要的是他舍不得将自己辛辛苦苦压担子挣来的钱随着几分钟的床板摇动就送到别人手里。他也不参与伙铺设的牌局打牌赌钱。三爹虽然十七、八岁就将三娘娶了回来,但起初八、九年,三娘一直未为他生一男半女。
三爹既肯干、又节俭,家庭人口又“素净”(当地的土话,意为人口少、易于计算),这就使他有了些余钱剩米,也就是有了一点积蓄。就这样,几年后三爹终于买下了一片虽然偏远一点、虽然较为荒芜,但价钱却便宜的茶山。
花了一个冬天,三爹将那块荒芜的茶山垦复了。他又听人说在新垦复的茶山上种荞麦会有好收成,于是就在自己的茶山上种了荞麦。果然,荞麦的收成不错。辛勤垦复的茶山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油茶树果实累累,茶油产量成倍增加……。
三爹就是这样干着。他既比自己大哥修觉勤劳肯干,又比自己二哥修麟精明能干。不过还有一点也许更为重要,那就是三娘的肚皮不争气,生了儿子嗣平以后就没了作为,而不象二娘那样接二连三地为二爹的家庭添丁加口,直添得家里屋徒四壁、隔夜无米。
由于家里嘴巴少、消耗少,总的来说由于家庭的物资生产大于人口生产(大爹、二爹家却正相反),就使三爹有了余钱来买第二片茶山、第三片茶山。就这样,十来年光景,三爹就拥有了三片产量颇高的油茶林。接着,三爹又陆陆续续买了些田、买了些土,还建了一幢新屋,随后又讨了一房小老婆。不过,还没有等到小老婆为他生儿育女、繁衍人口、分薄家产,就解放了。
土地改革时,三爹的大多数田土和茶山都分给了别人,小老婆也改嫁他乡。由于三爹土地改革前已拥有较多的田土茶山,还讨有小老婆,所以乡亲们私下议论说,按三爹的家产,他完全够划地主。而三爹之所以没有被划为地主,是因为他侄儿“马拐”和二哥修麟两家帮了他。马拐与修麟,当年是岭下村的“土改根子”,土改工作队的萧队长那时就住在修麟家里。
“当年萧队长最信任二娘!”“眯子哥”这位比三爹只小四、五岁,辈分却低一辈的老实本分的老贫农这样告诉我。
二娘是二爹修麟的老婆。虽说早两年才去世的修麟是个老实巴交的男人,但二娘却是个泼辣强悍的妇女。我刚到生产队时,二娘虽然已是一付病病歪歪的样子(其实那时她还不到六十,但由于一场病后治疗不彻底、营养又没跟上,所以身体垮了),但与媳妇吵架时却仍旧“中气十足”,不但嗓门照样很高,而且“口才”也相当不错,可以说是能言善辩。看得出来,她曾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
乡亲们关于三爹家庭成分的这些议论我起初半信半疑。不过后来我完全相信了。之所以完全相信,是因为我亲耳听到二娘在骂三爹的儿子、生产队会计嗣平时说起了此事。
嗣平是队里的会计,铁算盘。但岭下生产队会算计的不只他一个人。他的两位堂兄弟,也就是二爹二娘的儿子嗣俊、嗣美两兄弟在这方面比他一点都不逊色。
嗣俊、嗣美两兄弟一个是大队的副大队长,在大队负责锡矿场工作,一个常年被公社、大队调去干一些修渠道搞测量的闲差。他们不在生产队干活,但要在生产队记工分,而且要记最高的工分。所以为工分的事他们常与队里发生矛盾,尤其是与会计发生矛盾。
一天傍晚,嗣美与嗣平又为工分吵了起来,而且互不相让。听见他们争吵,听见嗣平不让着自己的儿子,二娘怒火冲天。她拖着一双小脚,支撑着病病歪歪的身子走到门边,扶着自家的门指着侄儿嗣平破口大骂,“你这忘恩负义的家伙,你当了会计神气什么?土改时要不是我们帮你家,你家早划成地主了!”。
听到自己伯母的叱骂,嗣平的脸胀得通红,却并不敢回嘴。三爹听到嫂嫂在骂自己的儿子,也连忙从屋里出来骂嗣平:“你按公社、大队开来的条子给他们算工分不就行了?吵什么呢!”。
嗣平灰溜溜地进自己屋里去了,但嗣美气仍未消。那天晚上我到他家去坐时,他仍旧气鼓鼓地对我数说嗣平的不是,说“嗣平癞拐真是不识好歹!土改时,要不是我家帮他在土改工作队那里说好话,他家能只划个富裕中农吗?……”
嗣美、嗣平两叔伯兄弟的这次吵架,不但使我相信了乡亲们对三爹成分的议论,也使我对土地改革运动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从三爹和他的兄弟们分家二十年后家产和阶级成分的变化,我也开始认识到,一个人属于哪个阶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使一个人阶级地位发生变化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