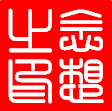葬 婴
我记得很清楚,事情发生在“三月三”。
两天前就听说界上的贞英生了个儿子,还是她自己接的生。她老倌仁福很是神气地到处现了一下面,接受大家的祝贺与恭维。他把当赤脚医生的小娅叫了上去。
那时“计划生育”已逐渐家喻户晓,政府也开始有了些强硬措施,比如已生了二男三女的大队会计就去做了结扎,说是干部要带头。人家笑他被劁了猪,不作用了,他讪讪道:“哪里,比原先还凶火得多。”幸亏是干部,否则,说不定会被当众脱了裤子,看家伙。
队长两口子的脸色很难看,他们各是男社员与女社员中最聪明、最能干的人,但这事就是不行,女孩一个接一个地生,三年前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没几个月又走了。 队长整整三天没有起床。
女知青都到界上去看望,她们都是未来要做母亲的人,热心,关心,担心,也就显露得很真切。小娅一直没有下来,饭没回来吃,觉没回来睡,因为包衣还没下来。贞英已有了生命危险。
日子在简单乏味中重复,与此同时,一些生命哇哇坠地,一些生命悄然离去,人们浑然不觉。唯有那些身陷其中的人,或大喜,或大悲。队里的生产照常,我出工照常。只有有仁福和小娅陪伴着贞英,在与死亡进行无力的抗争。
界上陆续传来消息:
贞英的血要流尽了;
小娅总是催仁福去公社医院请正规医生,仁福则总是吱吱唔唔,不置可否;
贞英快不行了;
小娅下山了,仁福的妹妹陪着去的,天高月黑,两人打着火把,来回奔袭四十里;
包衣下来了;
最后的消息是,那小男孩死了,死于那把剪脐带的锈剪刀。
三月三,吃过中饭我正要出工,仁福匆匆从界上下来,直冲我说:“颂平,这个忙,你非要帮了!”
“什么忙?”我见他一脸凄楚。
“那细伢子,”仁福眼睛望着地说, “累、累(lia)你帮忙埋了。”
我大吃一惊,也大吓一跳,埋死人!怎么找上了我?
仁福还是盯着地说:“你心好,又喜欢细伢子,只有、 只有你合适。”
我转过背,不忍听他带哭的哀求。仁福连忙又说: “队长答应了,跟你记半个工。”
“好吧。”我长叹一声,跟着仁福上界。一路碰到的人都默默无语地望着我,仁福头垂得更低。我听说过,谁的婴孩死了,自己是不能去埋的,否则那小东西又会来投胎,然后再死一次。于是我心里也就升起一种阻止灾难的责任感来。
仁福屋里昏暗杂乱,充斥着恶心的血腥气。“累你帮忙了。”一个叹息样的声音从黑暗中溢出,我循声望去,被柴烟熏得墨黑的帐子里,贞英脸色腊黄,几天不见,风干了一般,完全走了形。我点点头,怕开口。
仁福朝地上指指,一张卷起的杉树皮,伸出两只也是蜡黄的,风干了一般的小脚,旁边还有一滩淤结的乌血。靠墙立着把锄头,我正要去拿,被仁福拦住: “锄头我来扛,你背这个。”他指着树皮。我头皮发麻,又不敢问,弄不好又犯了禁忌和规矩。
“累你帮忙了。”出门时,贞英那幽灵般的声音又响起。
仁福扛锄头在前,我夹着树皮随后。仁福不作声,我也不开口。只是那树皮,夹松了,生怕里面的东西掉出来,夹紧了,又能分明感触到那软弱的一团,夹累了,也不敢扛到肩上,实在害怕和那东西脸对脸。冷汗、热汗交替流淌。
山越来越深,树越来越密,哪怕有一丝微风,也会引发松涛呜咽,令人毛骨悚然。不知走了多久,仁福终于停下,指着一小块空地说:“就在这里。”我忙放下树皮,坐到一边出粗气。
“你挖。”仁福把锄头递给我,“嘿,我挖不得。”
我只得起身,弯腰挖起来。土里尽卵石,一锄下去,锵锵作响。脱了几件衣服,出了一身大汗,总算挖下去两尺多深了。我停下,问:“够了吧?”
一直蹲在旁边发呆的仁福说: “还挖几下。太浅了,怕豺狗叼。”我心头一紧,又接着挖。终于仁福点了头。我丢下锄头,拿起树皮往坑里放。
“慢点。”仁福说罢,掏出一个鸡蛋放到坑里,又点燃一张钱纸丢到鸡蛋上。火焰裹着纸片随风飘起,散成碎末,再纷纷落下。
我又要放树皮,仁福弯腰捡出鸡蛋,塞给我:“你吃了。煮熟了的。”
天啦,望着还沾满钱纸灰的小鸡蛋,我觉得它就是那个刚刚逝去的小生命,我吃得下吗?但又不敢拒绝,唯恐犯忌。我把蛋放进口袋,应付说回去再吃。
树皮终于端端正正放到了坑里,我正要盖土,仁福又是一声叹息:“可惜了一张好杉树皮。”
去你娘的!
我真不敢看到那张小脸,否则他会在我的记忆里晃悠一辈子的。我不再犹豫,飞快往坑里扒土。仁福无奈地摆摆手,不作声了。
地上隆起一个小小的土包。仁福口中念念有词:“莫再来了,求求你,再莫来了。
鸡蛋毕竟甘贵,回去后我把它悄悄混入灶上的地菜子煮鸡蛋。后来不记得被谁吃到了,只说这蛋怎么这样硬,不像是新鲜的。我不敢声张。直到今天才在这里坦白交待,但愿没有谁为此交上恶运。
第二天队长把我拉到一边问:“你何解去做这号蠢事?”我不解,队长不是还记了我半天工么? 他解说了半天我才明白,原来,这种事只能请那些夫妻和好、子孙满堂的人来做,送钱送物更是少不了的;可终归晦气太重,谁都借故推托,以防不测。
知道我的“报酬”只有一个鸡蛋,队长更是不平,恨恨地说:“这个抠鬼!仁福缺德哩,他要害你断子绝孙哩。”
我苦笑:“我这一辈子还不晓得有婚结冒。”
1983 年,我带着四岁的儿子,回到已离别九年的队上。山水依旧,人已不同。细伢子长成小伙子,姑娘们都远嫁他乡;一些人去世了,其中竟有四十刚出头的贞英。
附注:此文刊于《我们一起走过》(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