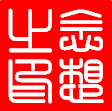彭姨是曾经文庙坪小学的一名校工,也就是学校食堂里搞饭的大师傅。原来是下黎家坡靠床单厂口子上粉铺里的女老板,自从晏大蔼姐调走后,也不晓得是凭了么子关系顶替别人搞得学校里来的。
彭姨那时四十岁左右,一副五大三粗男子汉胚子,满脸的横肉,嘴巴厚手板厚,一双鱼泡眼秋年四季往下面搭起,假如一抬眼睛的话,定会把你赫一跳,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肯定就是要骂人哒。而且她骂人是不看对象的,不论是校长、老师或是家属子弟,只要她认为是不合理的人和事,也不管是么子场合,那一口夹着长沙尾子的临湘腔就必定会把你骂得狗血淋头。
彭姨冒得么子文化,想得哪里就讲得哪里,讲嘎哒就讲嘎哒,骂嘎哒就骂嘎哒,从不考虑后果。因为是正式职工,做事又踏实卖力,作为小知识分子的老师们虽然常常挨她的骂,受点子委屈,也实在是奈何她不得。
彭姨有的是力气,一把大铲子和起煤来虎虎生风。而且她一双厚厚的胖手生来就不怕“哦”,澡盆直径大的饭甑上嘎大气以后,别个都不敢拢边,她廊嘎子筐一瓢冷水,一声嘿!“闪开!闪开!”面不改色饭甑就被端得一边克哒。
那个时候我最不情愿又不得不硬起头皮去做的事就是克食堂里蒸饭端饭,老师或家属们都是自己送米克蒸。每次我把蒸饭的钵子和坝缸兑好水放入饭甑里的上面一层,彭姨总是要利用自己的特权重新调整一遍:“你咯扎鬼崽子哪里咯自私罗,只晓得图自己方便。走开走开!”跟哒那号唆话子就一路路的就来嘎哒,恶彪彪的搞得你根本冒得还口的机会。
我们细伢子对彭姨既怕又恨,搞又搞她不赢,得又得罪不起,当面客客气气喊她彭姨,背后哈骂她做猪婆。经常搞些恶作剧来阴害子害。把她的铲子“给“起,把她的煤耙子霸塞得煤里面,要么在刚刚上气的大锅里又兑一瓢冷水,有回子几个人干脆爬得屋顶上把她的烟窗眼堵得严丝密缝,熏得厨房里烟直个艮。每回做嘎咯些鬼路径以后彭姨都要拍手跳脚骂得咯昏天黑地,她基本上也猜得到是哪几扎伢子害她,冒得证据就只好下恶咒。我们随她俄实骂,都暗暗的一边躲哒笑,感觉得咯样搞哈子才心里才过瘾,解哒点丫子恨。
有一回我玩过哒头冒做作业,娘老子检查书包发现哒气得捶嘎我一顿,我晚饭都冒恰跑得厨房里以前的一间老糠房里面躲嘎一晚,一清早彭姨进来拿东西发现哒我。一晚迷迷糊糊睡得老糠里面,肚子又呐瘪的,肯定是一副灰溜溜的样子。当时我都有些不相信自嘎的耳朵哒,彭姨一改平时的凶神恶煞:“伢子哎!你俄改躲得咯里罗,赶快出来,出来罗。我克跟你妈妈讲好话,她听我的。”我虽然很不情愿,还是磨磨蹭蹭走哒出来,被她带到厨房后背她住的小屋里,炒哒一碗蛋炒饭要我恰,我硬是冒动一哈筷子。她怕我又跑出克,临走时把房门反搭起。过嘎冒好久,门吱呀一声开了,她二妹子秋秋端哒两扎热喷喷的包子走起进来。
彭姨膝下冒得崽,只有两位千金。大妹子继承了她的遗传因素,皮肤倒是白,也是腰大臀园,嘴巴一翻起,冒得么子看像。二妹子秋秋应该是象她牙老倌,倒是冒得一点她娘老子的影子,性格也温柔得多,生就粉脸红唇,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按现在的港法真的是顾盼生辉。彭姨家里我也就只对秋秋的印象特别好,港句老实话,我小时候确实对秋秋萌生过一丝朦胧的、别样的、道不明的情愫。加之那个时期恰包子对我们咯些细伢子来港是极具诱惑的事,紧关肚子咕咕叫起来哒,我迟疑片刻,逮住两扎包子大嚼起来。秋秋屏住气,眼睁睁的望哒我一鼓作气恰完包子,兴奋得一路跑起出克,对哒外面大喊:“妈妈哎!他恰嘎哒,他恰嘎包子哒咧!”咯时候彭姨进来哒:“鬼伢子哎,莫逗你娘老子生气噻,你看她好不易得罗,老倌在株洲劳教,每天累得要死还要“卤”你们三扎细伢子,好不容易罗。”我从挨打到冒恰饭冒睡觉都冒哭过一声,听到这番话,尤其是出自彭姨之口,终于忍不住眼粒水流出来哒。
从那以后凡数捉弄彭姨的事我再也冒参与过,彭姨还是以前的秉性,直来直克,大家还是奈何不了她。表面上对我和对大家都是一样,不过我能够感觉到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的看似无意识的关切。文革中搞武斗我从三楼上跳下来绊伤哒脚,肿起好高,搭帮她廊嘎拿一瓶红花油给我天天揉脚,很快就好嘎哒。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除我下到靖县,大老妹下到汨罗,其余的全家人被清理阶级队伍遣送到边远的湘西龙山。垩梦般的一次次运动造成不少人扭曲了心态,对于我们家的遭遇,一些人庆幸,一些人看险,只有彭姨等极少数人从来冒歧视过我们,诚心的同情我们家的悲惨遭遇。她不懂得么子大道理,经常挂得嘴巴边的一句话就是:“她屋里老李实在是个老实人,不晓得么子鬼,搞得园根还连累哒一屋。”
我回城后彭姨已经退休哒,只在上世纪八几年看见过她一次,因为严重的糖尿病,早已瘦得不成形,加之大外孙伢子吸毒耗尽哒家产,当年的中气已荡然无存,只有我和她港起我小时候的故事的当口,才能从她干涩的眼神里掠过一丝曾经的希翼的闪光。
彭姨到底没有拗过病魔,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逝世于糖尿病。
彭姨其实是芸芸众生中一个极其平凡的小人物,不管她属于么子阶层的人,也不管我小时候曾与她有过么子过节,更不管其他的人怎么看待她。从她后来对我及我家里人的作为及态度,我看到了她真正的人性的一面,在我的心目中,她永远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
彭姨那时四十岁左右,一副五大三粗男子汉胚子,满脸的横肉,嘴巴厚手板厚,一双鱼泡眼秋年四季往下面搭起,假如一抬眼睛的话,定会把你赫一跳,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肯定就是要骂人哒。而且她骂人是不看对象的,不论是校长、老师或是家属子弟,只要她认为是不合理的人和事,也不管是么子场合,那一口夹着长沙尾子的临湘腔就必定会把你骂得狗血淋头。
彭姨冒得么子文化,想得哪里就讲得哪里,讲嘎哒就讲嘎哒,骂嘎哒就骂嘎哒,从不考虑后果。因为是正式职工,做事又踏实卖力,作为小知识分子的老师们虽然常常挨她的骂,受点子委屈,也实在是奈何她不得。
彭姨有的是力气,一把大铲子和起煤来虎虎生风。而且她一双厚厚的胖手生来就不怕“哦”,澡盆直径大的饭甑上嘎大气以后,别个都不敢拢边,她廊嘎子筐一瓢冷水,一声嘿!“闪开!闪开!”面不改色饭甑就被端得一边克哒。
那个时候我最不情愿又不得不硬起头皮去做的事就是克食堂里蒸饭端饭,老师或家属们都是自己送米克蒸。每次我把蒸饭的钵子和坝缸兑好水放入饭甑里的上面一层,彭姨总是要利用自己的特权重新调整一遍:“你咯扎鬼崽子哪里咯自私罗,只晓得图自己方便。走开走开!”跟哒那号唆话子就一路路的就来嘎哒,恶彪彪的搞得你根本冒得还口的机会。
我们细伢子对彭姨既怕又恨,搞又搞她不赢,得又得罪不起,当面客客气气喊她彭姨,背后哈骂她做猪婆。经常搞些恶作剧来阴害子害。把她的铲子“给“起,把她的煤耙子霸塞得煤里面,要么在刚刚上气的大锅里又兑一瓢冷水,有回子几个人干脆爬得屋顶上把她的烟窗眼堵得严丝密缝,熏得厨房里烟直个艮。每回做嘎咯些鬼路径以后彭姨都要拍手跳脚骂得咯昏天黑地,她基本上也猜得到是哪几扎伢子害她,冒得证据就只好下恶咒。我们随她俄实骂,都暗暗的一边躲哒笑,感觉得咯样搞哈子才心里才过瘾,解哒点丫子恨。
有一回我玩过哒头冒做作业,娘老子检查书包发现哒气得捶嘎我一顿,我晚饭都冒恰跑得厨房里以前的一间老糠房里面躲嘎一晚,一清早彭姨进来拿东西发现哒我。一晚迷迷糊糊睡得老糠里面,肚子又呐瘪的,肯定是一副灰溜溜的样子。当时我都有些不相信自嘎的耳朵哒,彭姨一改平时的凶神恶煞:“伢子哎!你俄改躲得咯里罗,赶快出来,出来罗。我克跟你妈妈讲好话,她听我的。”我虽然很不情愿,还是磨磨蹭蹭走哒出来,被她带到厨房后背她住的小屋里,炒哒一碗蛋炒饭要我恰,我硬是冒动一哈筷子。她怕我又跑出克,临走时把房门反搭起。过嘎冒好久,门吱呀一声开了,她二妹子秋秋端哒两扎热喷喷的包子走起进来。
彭姨膝下冒得崽,只有两位千金。大妹子继承了她的遗传因素,皮肤倒是白,也是腰大臀园,嘴巴一翻起,冒得么子看像。二妹子秋秋应该是象她牙老倌,倒是冒得一点她娘老子的影子,性格也温柔得多,生就粉脸红唇,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按现在的港法真的是顾盼生辉。彭姨家里我也就只对秋秋的印象特别好,港句老实话,我小时候确实对秋秋萌生过一丝朦胧的、别样的、道不明的情愫。加之那个时期恰包子对我们咯些细伢子来港是极具诱惑的事,紧关肚子咕咕叫起来哒,我迟疑片刻,逮住两扎包子大嚼起来。秋秋屏住气,眼睁睁的望哒我一鼓作气恰完包子,兴奋得一路跑起出克,对哒外面大喊:“妈妈哎!他恰嘎哒,他恰嘎包子哒咧!”咯时候彭姨进来哒:“鬼伢子哎,莫逗你娘老子生气噻,你看她好不易得罗,老倌在株洲劳教,每天累得要死还要“卤”你们三扎细伢子,好不容易罗。”我从挨打到冒恰饭冒睡觉都冒哭过一声,听到这番话,尤其是出自彭姨之口,终于忍不住眼粒水流出来哒。
从那以后凡数捉弄彭姨的事我再也冒参与过,彭姨还是以前的秉性,直来直克,大家还是奈何不了她。表面上对我和对大家都是一样,不过我能够感觉到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的看似无意识的关切。文革中搞武斗我从三楼上跳下来绊伤哒脚,肿起好高,搭帮她廊嘎拿一瓶红花油给我天天揉脚,很快就好嘎哒。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除我下到靖县,大老妹下到汨罗,其余的全家人被清理阶级队伍遣送到边远的湘西龙山。垩梦般的一次次运动造成不少人扭曲了心态,对于我们家的遭遇,一些人庆幸,一些人看险,只有彭姨等极少数人从来冒歧视过我们,诚心的同情我们家的悲惨遭遇。她不懂得么子大道理,经常挂得嘴巴边的一句话就是:“她屋里老李实在是个老实人,不晓得么子鬼,搞得园根还连累哒一屋。”
我回城后彭姨已经退休哒,只在上世纪八几年看见过她一次,因为严重的糖尿病,早已瘦得不成形,加之大外孙伢子吸毒耗尽哒家产,当年的中气已荡然无存,只有我和她港起我小时候的故事的当口,才能从她干涩的眼神里掠过一丝曾经的希翼的闪光。
彭姨到底没有拗过病魔,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逝世于糖尿病。
彭姨其实是芸芸众生中一个极其平凡的小人物,不管她属于么子阶层的人,也不管我小时候曾与她有过么子过节,更不管其他的人怎么看待她。从她后来对我及我家里人的作为及态度,我看到了她真正的人性的一面,在我的心目中,她永远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