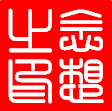木排游渠江
还有一段从生产队到会同岩头水文站的几十里乘木排的经历,那是我的渠江情结中不可缺的一部分。
在长沙宿舍的贴隔壁,住的是一位曾为毛主席游湘江测水文资料的刘修吾叔叔。他家的独生女小兰与我妹妹一样大,也是下放的对象,周姨没有工作属“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对象。刘叔叔被下放到基层,由水文总站调到了会同岩头水文站。于是全家都到了那里,母女两的户口就落在了岩头水文站所地的生产队,住在水文站内,在生产队出工挣工分,在那个艰难年代,刘叔叔苦心经营总算保持了一个完整的家。长沙的贴隔壁邻居变成了“我住渠江头,君住渠江尾”。同饮一江水的刘叔叔经常要到靖县的水凉塘水文观测点来,他得知我们兄妹住在马路边,本可以坐班车来往两地之间,他常弃车不坐,而骑自行车往返。为的是顺便看顾我们兄妹。我兄妹也因得到父辈的关怀而感激,想去向刘叔叔、周姨问候请安之心久藏于心。
有一天,腰上系着一把带刀鞘壳柴刀去出工,看到渠江上漂来两带小木屋的木排,放排的正是队上派出抓副业的其坤、其连两兄弟。打几声哦喝,我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说是到洪江去,问我去不去。我向同行的人打过招呼后,二话没说脱掉衣服,把衣服和柴刀举在手中,跳进水里,游到了他们驾的木排上。
这种送到洪江的木排,排扎得比较大而且结实正规,因有几天的水程,一般都搭建有小木屋,吃住都在排上,排的两头都有“招”(一根杉木头上钉有一小圆木棍用来把握,木尾上用竹片编成长方形的一块,象浆一样的专用划排工具,实际上就是用整根杉树作划水的大浆)招可以水平360度旋转,在两侧可用来划水,转到前后用来掌握方向起舵的作用。排上还带有篙子。上排后不远,就到了太阳坪的拦河坝。平时队上也卖木材到太阳坪木材站,扎成排后,并不要我们知青放排。就是因为有这个拦河坝。百多米宽的河面就剩下十来米宽的泄水口可以通过,泄水口落差大,水道又窄又短,水流非常急。木排不比船。它又宽又长,几乎是塞满了隘口而下,所以下去时必须保持前进的方向,下到底时还要绕开前方的岩石。平时也常看到过放木排的事故:因方向没有对准方向把排横在拦河坝上;没有绕开前方岩石撞散了排的事故。在泄洪道上出事故非常危险,搞不好是排散人亡。到太阳坪几年时间,这还是第一次乘木排过此泄水口。下口子之前,其坤就嘱咐我到木屋边去,抓紧东西保持身体稳定不要乱动。只见他时而前扳招,时而后扳招,对准方向后又拿起篙子冲到最前方,进入隘口后,木排急速由水平变成向前倾斜,木排剧烈摇晃起来,他毫无依靠站在排上,横持篙子中进入生死博斗状态,只见他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用篙子向左边的一块石头上一点,用力一撑,排好象改变了点点方向,过程时间不长,飞快的速度,剧烈摇晃的木排,惊涛拍浪的水花及急流发出的巨大响声,让人惊心动魄。木排很快又很安全的下了泄水口,重新变得平稳。其坤告诉我:他刚才用篙点左边的石头那一下,是生死招。点早了排就会向右方横走后面可能进不了口子横在坝上,点迟了前进方向不会改变,会被直冲到岩石上散排;点岩石的时机、用力的大小、撑多久时间、距离,都必须把握得准确无误。才能保证木排安全通过。
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才体会到队上不让我们知青放排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而联想下放到幸福大队的李兴邦、赖德礼,他们队上的人要看他们的险,让他们单独放排下太阳坪,没有人教,他们在在拦河坝前驾着排打了几个圈,不知道怎么放下去,只好看别人怎么下去,好在扎的木排小,麻着胆照别人的样子放下去,也成功了。虽说是一种锻炼,但是也是拿他们的生命当儿戏。相比之下更体现了我们队上对知青的关怀,心里非常的感激。
过此泄水口,绕太阳坪,过土溪铺,经过会同连山几十里的路程,看足了两岸的秀丽风光,青山绿水,虽比不上桂林的奇山桂林的水,但也大饱眼福。一路又听他扯谈,教我怎样识别水心,选择航道,如何扳招,如何撑篙子。再没有遇到危险的地段,一路上也见识了放排人的辛苦,他们时不时要扳招来掌握方向,时而要撑篙子来提高速度,在不平的木排上来来回回的走,很少有休息的时候,尤其是他们不能穿鞋,脚丫子长期泡在水中烂得见红肉。
到岩头水文站后,刘叔叔及全家很热情的招待了我这个两手空空的隔壁邻舍和两放排人。当晚我留宿在岩头站内。第二天我背着那把柴刀,问清了靖县甘棠的方向,一个人朝着那个方向过深山老林,仗着背后的柴刀壮胆,几十里山路几几乎没有遇到人,逢山过山,逢水过水,有时被山林中突然的怪鸟叫声骇得汗毛倒竖,但总算是与魚与兽无缘,连蛇也冒见一条。几个钟头下来,终于从山顶上看到了甘棠乐群一队。这一趟乘排漂渠江最大的收获还不在玩得痛快与走得惊险,而是在岩头水文站发生的一些事,差一点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留宿后的第二天,水文站的职工来上班了,刘叔叔把我带到他们面前,问他们认识不,谁知他们马上都能说出,我父亲名字,并认定我是他儿子。我父亲64年故去,近十年了,但是他们都印象非常深刻,说我太象我的父亲。而水文站的莫站长正生病住在附近医院,刘叔叔又带我到了医院看莫站长,也是一见面就认出我是谁。我还想这些人我全是不认识的,看不看都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在意。到了七四年底,我妈妈单位来补员,已确定了我被招工到长沙市运输公司。第二天,公社又来通知要我到公社去,说是招工的人有事找我,我还以为又有变故,到公社一看,来的人不是长沙运输公司的人,而是岩头水文站的莫站长,我到医院去看过他,他此次招工就是冲着我来的,而前一天,我的档案材料被运输公司拿走和手续都已办好。他迟到了一天,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因为是熟人,说话就方便多了。他问我还有什么水电系统的人在此,我告诉他在甘棠平原有一个周围围的女孩,他回答说已经招到手了,是不是还有别人。我大着胆子向他推荐了晓阳,谁知他一听说晓阳的名字,就说他的政治审查过不了关,条件太差了,不能要。我再向他介绍我队的靖县知青李靖生,他又说靖生已找了农村姑娘,我反驳说找了农村姑娘不等于已经结婚,只不过是订婚而已。老莫听我这样一说,就着手对李靖生招工,最后与李靖生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不准抛弃农村姑娘,到时候一定要和农村姑娘结婚并不准离婚。否则就不招。靖生就这样在有约法三章的前提下招到了水文站。2005年回靖时才知道,他也很认真的执行了约定。仍是那乡下妹子为妻。妻子被照顾在怀化水文站扫地。刘叔叔让我去看一些不相干的人其实是在帮我打招工前的底子,用心很良苦,要不是老莫迟到一天,使我与水文站失之交臂。我可能子承父业。也不会到长沙拖板车。但是我非常感谢刘叔叔对我的关心。
从浮桥上游十几里漂流下来,又从浮桥起坐船几十里游到了贯宝渡。贯宝渡到生产队的几里水路,那时经常走。再往下到乘木排几十里到岩头水文站。现在回想起来,知青中能如此畅游渠江近百里者是不是还有别人,只怕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