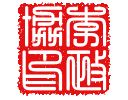在岭下生产队,我完完全全生活在淳朴的贫下中农中间。共同的艰苦劳动和困苦生活,使我与他们的心连在了一起。由于把我看成是他们中的一员,生产队贫协组长马拐甚至自作主张地为我作介绍,要把他一个亲戚的女儿给我做老婆。我有几分不知所措,但稍微镇定下来以后,我礼貌地谢绝了他的好意。虽然我的谢绝也许有不愿意“真正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之嫌,虽然我的谢绝也许使马拐有些扫兴,但我与他之间,与其他贫下中农之间却并没有因此产生半点隔阂。
夜晚吃过饭后,我常去各家各户串门、聊天。乡亲们忙完一天的活儿后,如果有时间,也总是到我的小屋来坐、来拉家常。
逢年过节,乡亲们会把他们做的糍粑、饺粑等这些他们自己一年到头也难得吃上一两回的年节食品送些与我分享。我从长沙探家回村时,也会带些乡下没有的点心给他们尝尝。他们家里来了客人常常会叫上我去作陪,一同喝上两盅他们自家酿制的红薯酒。同样他们没有钱打煤油点灯时,我会将我的煤油瓶提给他们。
虽然我已经完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外表上也已经象个农民,但这并没有使我的思想与极左路线的要求更靠近。
为什么会如此呢?
这是因为我发现,极左路线告诉我的中国农村、农民的过去和现在,与贫下中农告诉我的,与我自己在农村感受到的大相径庭。这不能不使我的思想与极左右路线的要求距离越来越远。
在地里劳动时,夜晚坐在村口的石板上闲聊时,乡亲们总喜欢谈他们过去的一些往事。就是乡亲们谈起的这些往事,使我认识了许多以前被掩盖了、歪曲了的事情。
(1)、乡亲们嘴里的“大跃进”和“苦日子”
在桩桩往事中,乡亲们最爱谈论的要数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乡亲们谈论大跃进虽然只是就事论事,但很明显,他们对大跃进持否定态度。
乡亲们说,大跃进那阵子,“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极其严重。本来是个好年成,但稻谷“倒穗”了、地里成熟的红薯烂了都不让收。劳动力全都抽了去大炼钢铁。结果钢没有炼出来,还把各家各户的锅也砸了,山上的大树也为烧木碳炼钢铁而砍光了。尤其是即将到手的粮食──地里已经成熟的庄稼没有及时收割,造成很大的损失。搞到后来,饭都没有吃,过起了“苦日子”。
在乡亲们嘴里,“大跃进”实际上是一场瞎胡闹,而“苦日子”则是大跃进的结果,它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造成的,至少在樟市公社、在桐木大队和岭下生产队,苦日子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
苦日子到底有多苦?乡亲们没有细讲。但妇女们都说,“苦日子”时,她们每个人的月经都停了,差不多人人都得了水肿病。身高体大、力气过人的“黑子古”就是得水肿病死的。没有粮食,人人都吃糠,结果大便拉不出来,要用手去抠。吃不饱,夜里饿得受不了,就跑到地里去偷生产队的萝卜吃。
“那时我们人人都偷过萝卜。我们都当过小偷”乡亲们说。
说到大跃进时的人物,乡亲们讲得最多的是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烂钵头”(这一带农民将那些好吃懒做、四处流窜,靠诈骗、偷窃过日子的人称做“烂钵头”)。
“烂钵头”是邻近的岗口大队人,“土改”起家。据乡亲们说“烂钵头”工作能力很强,搞行政命令、软硬兼施很有一套。同时“烂钵头”又能说会道,扁的他可以讲圆,圆的又可以讲扁。
搞大跃进、吃公共食堂,家家都不准养猪,结果过年时户户都无猪可杀。无猪杀就没有肉,就不可能象往年那样做猪肉肘子、猪肉丸子。过年都没肉吃令人人都感到沮丧。可“烂钵头”却在公社万人大会上口水横飞说“我们有‘萝卜肘子’‘萝卜丸子’……”。
不过,据乡亲们说,“烂钵头”最大的本事还是玩女人。因此关于“烂钵头”故事的最主要部分,是他如何玩女人,玩了多少。
“烂钵头”玩女人也是软硬兼施。他利用自己公社党委书记的牌子,施点小恩小惠便使一些妇女自觉自愿地陪他上床。而对那些不肯就范者,他甚至拔出盒子枪比着(乡亲们说“烂钵头”屁鼓上成天都挂着盒子枪),强迫不从者就范。
他每到一个大队,先搅动如簧之舌,叫男人们为大炼钢铁而通霄达旦地守在小高炉旁,而他在公共食堂吃饱喝足以后,就以听汇报谈思想为名,乘机纠缠他看上的娘儿们,胁迫人家与他干那事……。
当然,土改积极分子、合作化带头人、大跃进急先锋、一方父母官的公社党委书记“烂钵头”最终落了个“三开除”、回乡下种田的下场。乡亲们说,直到今天,即使是坐在汽车里经过后来已分成另一个公社的全义墟的地界(“烂钵头”在那里玩的女人最多),“烂钵头”也是埋起头躲着的,因为全义墟有很多男人说只要看到他就要用锄头挖死他。
大跃进的许多往事是苦涩的,但有一件事,岭下的乡亲们一讲起来就笑得合不拢嘴。
乡亲们说,涧对面的一大片旱土,原来是坪冲生产队的。大跃进时,因为吃公共食堂、搞共产主义了,所以个个生产队都嫌自己的田土多,都想划出一些给其他生产队耕种。坪冲生产队是个大生产队,人“强”,硬是要把涧对面那一大片地划归岭下生产队。而岭下人向来老实本分,在大队的劝说下,没有办法只得接受了坪冲生产队划来的那一大片地。
把自己的土地划给岭下生产队耕种,坪冲人开心极了。可不久,则轮到岭下人开心了。因为后来公共食堂垮了,又开始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多一大片土地使岭下生产队多收了不少粮食,而多收了粮食,当然就少挨一些饿了。
“后来坪冲人又想要回那片地,但我们坚决不给。‘当初可不是我们要占你们的,是你们自己硬要划给我们的’。要了几次要不回土地,坪冲人也不好意思再开口了。”
说起这件往事,岭下的乡亲个个比捡到宝还开心。但我听了这个故事却只有苦涩感。我从小就从书本中知道“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但大跃进却使农民不再爱是自己命根子的土地。对于报纸上经常吹捧的大跃进,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剌呀。
乡亲们的大跃进故事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它使我隐隐约约感到,多少年来,报纸、电台上一直极力吹棒的大跃进并不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它不单只是一场瞎胡闹,也是一桩大罪过、大灾祸。而这场灾祸的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伟大的领袖。
(2)、修觉与他儿子的故事
除大跃进的往事以外,岭下生产队的乡亲们也爱讲村里一些人物的旧事。乡亲们都说,岭下村的老一辈人大都身材魁梧,力气也大。这一点我既有几分相信,又有几分纳闷。
从岭下村唯一一个健在的老辈人“三爹”那里,我想老一辈岭下人可能高大魁梧。我身高
但是,岭下村现在的成年人为什么普遍只有
关于岭下村的过往人物,乡亲们讲得最多的是修觉。
修觉是生产队贫协组长“马拐”的父亲,高个子老汉“三爹”的大哥,据说他身材比三爹还要高大。
修觉走南闯北见过世面:他当过脚夫,又当过兵,还在汉阳的兵工厂以及水口山的矿务局做过工。修觉也心灵手巧,尤其善调五味,曾在福楷兄的父亲办在郴州镇的伙铺(即客栈、旅店)当过掌勺的大师傅。修觉还力大过人,三百斤的担子挑起就走,百多斤的担子挑他个三几十里路不用歇脚。
不过乡亲们说,修觉的最大特点还是嗜赌如命。
他打牌赌钱先是输光了自己从父母那里分得的、全家人赖以生存的田土,接着又输掉了栖身的房屋,最后,家里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灶头上的火钳也被他摆上了赌桌。为了筹钱赌搏,他曾决定将儿子马拐卖掉。只是由于族人(主要是福楷的父亲)阻挠才没有卖成。不可避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修觉最后死于贫病而没能活到象贫下中农翻身解放的日子。
岭下人议论得最多的另一个人是庆吉。
庆吉是修觉的大儿子,但他的命运与自己的父亲比,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庆吉在省汽车运输公司当客车司机,他开的车时常跑樟市、桐木这条线。庆吉不但是岭下人的羡慕对象,也是全桐木人的羡慕对象。因为那时乡下人羡慕所有“吃国家粮的”城里人,尤其羡慕司机。不过乡亲们说,庆吉现在虽然风光,但以前却是另一个样子。
据乡亲们说,庆吉当年在他父亲赌光了家产、死于贫病后,也走上了与自己父亲同样的道路。他不象弟弟“马拐”那样去给人做长工打短工,以便养活自己、妹妹及继母,而是成天脚踏一双破草鞋,腰系一条烂汗巾往墟上跑,与在墟上打牌赌钱的二流子为伍。
“那时我们都以为他也会象他老子那样,有一天会倒毙在哪条田墈脚下。”乡亲们都这么说。然而,庆吉却并没有倒毙在哪条田墈脚下。四八年(1948年)他“卖壮丁”当兵以后,不久就在一次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并由此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抗美援朝时他又成了志愿军战士。在部队,庆吉学了文化、学了技术,复员以后就成了省汽车运输公司的司机。不但他自己成了光荣的工人阶级,他全家也都成了吃国家粮的城里人。
虽然有的穷苦人“卖壮丁”是出于无奈,但据常给我讲自己侄儿庆吉往事的三爹说,“卖壮丁”也常是一些二流子干的勾当:他们收了人家七、八十块光洋后,就替人家去当兵。然后,他们再从军队中开小差逃出来。有的人,过后又将自己重新“卖”出去。虽然乡亲们说起庆吉沉迷于赌搏以及“卖壮丁”的往事既不带贬意也不带褒意,不过却使我了解到今天作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一员的庆吉司机,过去的生活却并不见得那么光彩。修觉和庆吉两父子的故事,使我感到人以及人生的是非曲直用当时的阶级理论是很难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