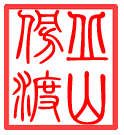第 2 楼

浅谈吃,小吃及江永的小吃

肯怕没有哪个人敢说不喜欢吃,我喜欢吃。我也相信大家也都一样 。古语说:“食色性也。”不说色,单讲“吃”。社会从古到今,人生从小到大,一个“吃”字就对人充满诱惑,因为不论是富人穷人,男人女人,小儿老者,一生中,都曾为吃而发愁而烦恼,也因吃而快乐而兴奋。特别是我们这一代有过吃不饱的经历,那时想吃有没有吃,近年来吃饱了,又想吃得更好更营养。“吃”真让人百谈不厌,因为它给人最基本、最重要、最经常的享受,这个享受不因次数太多而递减,不因过程复杂而厌倦,
不过,这种感觉也不尽然,这些年来,我们的日子的确好了很多,这个迷宫似的城市,让人看相同的景物,走相同的路线,到相同的目的地,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工作,就是吃饭,这些年来,工作上的应酬也比原来多很多,也常到相似的餐馆就餐,接受迎宾小姐处处一样的的鞠躬,看服务生千篇一律的微笑,在全封闭的落地玻璃包厢中接受相同的服务,就是菜肴细细想来,湖南人喜欢跟风,总又是那样雷同,当初享受中的确使人有一种莫名的快感,但是,久而久之,人们会很快厌倦这样的生活,陪客和应酬使人感到很辛苦,心中又有一种无奈的寂寞,灯红酒绿却常常有一种身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觉。特别是现在营养过剩,富贵病流行,那些鱼肉大餐看见就叫人生畏,吃饭,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头等问题,早已变得和庸碌的人生,平淡的生活一样,成为填饱肚皮、提供动力的一道工序,哪里会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啊!
现在退休,知青每次聚会,老知青重逢心中又油然涌动着许多激情,吃被赋予新的含义,是我们相聚的载体,使人感到充满欢乐,举杯把盏之间我们聊得很多的就是第二故乡,青春的回忆总是那样顽强,闲话之间我常常想到江永的小吃。
谈起小吃,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乔羽先生的故事,乔羽先生远去台湾、从未谋面、并无联系的哥哥,有天深夜打来电话,泣不成声,只有一句:兄弟!我想吃家乡的生煎包子糊辣汤,可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哇!第二天,台湾来电,老人仙逝。临逝时,他那凝聚一生的思归浓情,都化作了对故乡小吃的眷恋。中国人常把对故土的思念直接转变为对故乡小吃的依恋啊!
我是在长沙出生的,又在长沙长大,本应该对长沙的小吃情有独钟,其实不然,那时母亲一人抚养我们兄妹俩人,收入微薄,日子十分艰难清苦,从来没有带我们去吃过火宫殿的,姊妹团子双燕馄饨奇珍阁的鸭李合盛的牛肉等长沙名小吃基本没有印象,我绝没有责备母亲的意思,回想起他还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把我们抚养成人,我眼里总含着感恩的泪水,下放到江永以后,那时年轻,干的农活,正青春年少,想吃会吃又没有吃,更难得有大鱼大肉的会餐,那些独具当地特色的小吃就越发使我们印象深刻了。

今年五月,我和我们公社的一行人回到江永,去时就在车上将江永的小吃聊的垂涎欲滴,引起很多温馨的回忆,记得2004年江永知青下放四十周年,八百知青回江永,回长时将江永县城整条街上的叶子粑粑,粽子全卖光了,大家大包小包提上车,可见对江永的小吃不是我一人情有独钟,当年天心阁的知青酒楼业组织了江永的叶子粑粑等特产,大家闻讯也趋之若鹜,餐上一上就是了好几盘还不解馋,往事并不如烟,我还记得,当年的师傅娘,包了叶子粑粑,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却一定要留一些给我,一定会把我叫了去,一定要看着我吃完了,才让我走,那眼神我至今难忘,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使我感到了人世的温暖。我们村子那时是清明包粽子,那是粮食不够吃,粽子还是要包,乡亲们也常常会叫你进屋送一个粽子给你,饥肠辘辘,几口吃下一个粽子,回想起来,那天然清香的粽子,吃的时候用黑手一擦一剥,吃完后香甜到了心里,走出来对着天空大地,对着太阳月亮,对着花草林虫,还有身后的黄狗,那时候,我真感到是一只快乐鸟,一只真正的快乐鸟,今天想起的确有点滴水之恩的感觉。还记得那时集市上的油炸的花生团子,清脆香甜,那时的村姑很纯朴,你说她炸得好或许你多买了几个他会露一口洁白的牙齿笑容可掬得加你一两个。。。那时真是共产主义,谁有钱都会卖几个花生团子,带给没有来集市的知青吃,回想那时赶集回家路上,一路笑语喧哗,青春的心声,如清泉淙淙,又在我耳边絮语呢喃。。。
那次从江永回来,回程中大家就急着去市场买东西,江永的桐叶粑粑,和粽子,每个人拎了一包,还买到了久违的油炸花生团子,其中还有乡亲在我们要发车时,还送来了粽子等,直往我们车里塞,使我们非常感动,当我将这些小吃带到家里,母庆吃着又大味道又好得江永粽子,他问我多少钱一个,我讲一元钱四个,他说了一句,这么好你为使么不带一百个回来!我真有点愕然!我的母亲也被江永的货真价实的粽子迷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