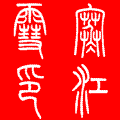我出身在国民党少将军医处长的家庭。爷爷早年留学日本,现在看来应不是十分反动的家庭。父亲是共产党外围组织成员,策反胡宗南未成,47年就离队回家在天心阁下开私人诊所,解放初期被王首道推荐去省委、省政府领导们子女就读的”育才”学校当校医,后调任长沙儿童保健所所长,再后调卫生厅,59年病故,免受“文革”之苦。
我在仙桃电排时,永安大队张九生,仙桃大队陈政才受公社委托去长沙调查,在公安局查到档案,说没问题,才清白了我自己的“黑七类”有多"黑"。这些无须再表露什么,那些影响我一世"不撑眉”的罪名和我肉体一样行将就木,大半辈子"背时”,再争什么“豪气”已毫无意义。遇到知青朋友,才有了倾诉的地方,而今的“小莉子”还有哪个愿听“老甸甸”讲过去的事情咯!
我何解要讨乡里堂客呢?一句话是讲不清楚的。我搭帮她给我一个避风港,让我避开了很多歧视的眼光,远离喧嚣的闹市,使我静心做自己的事情。
我从小学习和品德是很看重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性格内向、属追求上进那个类型的人;属受到几大挫伤后还不放弃“重在表现”这线希望的那种人。我的几大挫折:
一是我哥,附中高47班高才生,团支部书记,1964年长沙市高考理工科第一名。结果金榜无名,下放江永.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
二是白沙街事件,说来好笑,我那时在红卫兵组织跟毛主席闹革命,67年国庆前夕,街道办事处一帮人不知奉谁的指使,半晚抄家,没抄出有价值的东西,发现桌上镜框内毛主席像后放了一张我爸的照片,就追问这个反动分子是谁,要揪出来示众。本来是我妹妹好意敬毛主席,一听到要示众,急得哭起来了,小妹子那受得了那样折腾,我就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不得了!出了大反革命事件,肯定是我妈后台,我那高才生哥争了几句,一起绑赴白沙街小学看管。进门我这主犯就被鞭刑,我不服,被绑在操场示众,批判。我妈受牵连被罚扫操场.扫到我受刑的树旁,细声说,他们讲什么都承认,免受皮肉之苦。沙阳老弟多方营救,都没挽回“最后一批出狱”的命运。我一肚子拥护革命形象,被一绳子捆得威风扫地。对我的心灵振撼可想而知!
三是班上那些红五类的歧视,对我们黑崽子们隔三岔五地被勒令洗心革面.给人有受不了的感觉。我曾坐在水陆洲过小河的浮船上,三四个小时望着河水流泪,苦想脱离红尘最痛快的方法。
下乡后我力求找到舒展自己人格,寻找摆脱人生困境的平衡点。很幼稚地认为找个贫下中农做老婆,希望在我后代那里冲淡一些黑色素,还能听毛主席的话,扎根一辈子。生产队又不嫌弃我出身不好,所以跟社会赌气、跟自己赌气、走上了一条不归长沙之路。这条路给我带来乐趣,也给我烦恼,远离城市的麻木,对山外世界变化的迟钝,拉大了我与都市的距离。我长沙儿时朋友叫我“乡干部”,我那黑亮的皮肤把我打扮得成为十足的农民。我见证了安乡的过去和现在,身上打下了基层农民的深深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