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网先锋论坛 (http://2007.hnzqw.com/index.asp)
-- 怀化知青 (http://2007.hnzqw.com/list.asp?boardid=70)
---- [原创]知青岁月[31~35] (http://2007.hnzqw.com/dispbbs.asp?boardid=70&id=26989)
-- 发布时间:2007/5/8 18:36:10
-- [原创]知青岁月[31~35]
知青岁月[三十一]
回到宿舍,我拆开信封一看,原来里面就是一条她们当地年轻女性都喜欢绣的绣花手绢,绣的是二朵红色的月季花,和一张写有她家地址的小纸条。
第二天早上上车时,我远远的看见了她,并朝她挥了挥手,就这样,我同她分别了。回乡后,我还是兑现了我的承诺,给她写过几封信,后来是她回信中告诉我,说她父母为她订了亲,她不满意,与家庭产生了矛盾,很苦恼,想我为她想办法,让她摆脱那困境。
我能够有什么办法帮助她解脱呢?
我一个外地知青,自己都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那还能帮得了别人。我只好劝她听天由命,不必与父母作无畏的抗争。并告诉她;“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此封信后,她也就再也没有给我写过信了,她不回信,让我也不便再给她写信,因此也就终止了联系。
这次到新晃后,我就没有坚持写日记了。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宿舍里的人大繁杂了,不像过去的就只有自己班里的几个人。
在这里,我们住的营房都很集中,因为是重新组合成的连队,全县各个公社的人都有,都是在三线上搞过那么久的人,熟悉后,都喜欢串串门,因此,宿舍里来往的人都比较复杂,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保存私人物品,日记本都只能放在枕头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翻看,也就不便于再写了。连我的来往信件在此都没有一封保留,看完后也就全烧了。因此,这一段的回忆也就不可能写得详细,也记得不太清楚,成了真正的回忆。
现在唯一保存的在新晃写的东西,就只有几首小诗,如下面这首在“风浪中航行”。
《在风浪中航行》
艰苦的生活使我们感到疲劳,沉重的修补地球让我们觉得辛累。
可我们的心却永远是那么的愉快,精神是这样的充沛。
我们的命运是这么的悲凉,我们的前途是那样的渺茫。
可我们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仍在与狂风巨浪的搏击的行航。
死亡,时时可能会在我们面前出现;尽管这生命对人只有一次,
可面对着死神,我们也将是放声大笑。
痛苦没有使我们失望;疲劳也没能叫我们懒散。
凶风恶浪没有让我们感到惶恐,命运也不能将我们束缚。
有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引路,有百万知音与我们相伴,
我们的生活永远不会孤单,困难也永远不会放在心上。
我们要像山林中的小鸟——快乐的歌唱,我们要像花丛的蜜蜂时刻辛勤的劳动
我们要像暴风雨中的海燕——勇敢坚强,我们要像蓝天雄鹰永远展翅翱翔
在这修补地球、改造宇宙的耕耘中,
献出我们全部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像金子般闪亮。
《怀念故乡》
晚霞映红了天空,鸟儿还在枝头啼唱。
微风从田野吹来,我的心啊—一飞向远方。
啊—一长沙!
我可爱的故乡!我的心永远向着你飞翔。
纵然走过无数的城市,也欣赏过多少美丽的风光
但我永远也忘不了你,我亲爱的故乡。
碧波荡漾的湘江水呀,翻腾着银色的细浪。
无数张满风帆的船舶,博击着风浪,在浩瀚的江水中航行。
“桔子洲”像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停泊在湘水中央。
乘风破浪;迎寒历暑,经历着世代炎凉。
风景优美的岳麓山,昂首座落在湘江的西岸。
响鼓岭、飞来石、五轮塔、白鹤泉,还有了汉魏最初名胜,和千年的书院
有多少人间美丽的传说,将它讴歌、传颂
青枫峡里爱晚亭,曾经有一代伟人在那里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东方红广场上,五星红旗在飘扬,
高大雄伟的领袖塑像,就屹立在广场的中央。
象江河的流水涛涛流入海洋,我的心像长上了翅膀,
向着你呀———故乡,愉快地飞翔。
啊——美丽的故乡,无论我离你有多么的遥远,
你的名字都将印在我心上。
晚霞映红了天空,鸟儿还在枝头啼唱。
微风从田野吹来,我的心啊—一飞向远方
《如令梦..;转战》
麻阳·辰溪·怀化三线千里转战。今日从何来,新晃城西渔市。此行此行,
农业战线会同。
我们离开新晃时应当是七二年的四月上旬,那时我们的任务已经全部完工,只等铁路工人铺轨了。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铺轨的机车始终没有等来,我们没有等到铺轨也就离开了。同时,我也结束了近一年多的民工生涯。



-- 发布时间:2007/5/8 20:37:38
--
三人,你真不错,把过去的小诗还留着,那时我也喜欢写些小诗,就是冒心留下,真遗憾。
-- 发布时间:2007/5/9 16:47:59
--
拜读了.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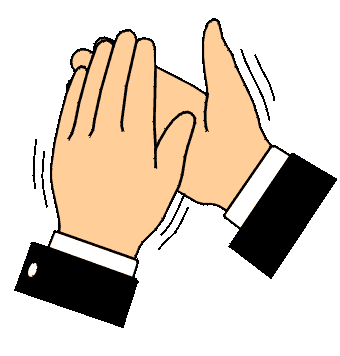
-- 发布时间:2007/5/15 23:01:11
--
知青岁月[三十二]
这次回乡是汽车将我们送回的,我们到公社时都快十点钟了,公社什么也没有安排,大家就只好连夜走回生产队。
记得这晚的天气很好,是春季难有的好天气。大半边月亮挂在当天的夜空,夜空中还飘浮着几丝的云彩。我们大队只有我一个人,因此也就只能是一个人回队。好得天空中有那一轮明月,能够照清楚那山间的小路,让我不至于要摸黑走那五里多路。
在农村搞了近一年,来住渡口也有几十次,过去也帮那摆渡的老者划过船,在划得不好吧,可也能够划得几下,这晚我就是自己独自划船渡的河。
山冲春季的夜晚并不寂静,有虫吱、蛙鸣和布谷鸟的啼叫声,偶尔还能听见几声“呵,呵”的当地人称作的鬼叫声,而实际却是猫头鹰的叫声。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那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呀,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我挑着行李,一路唱着这支歌,翻山越岭,穿垅过港地走进了生产队,走进了离开近半年的家——低矮的小仓房。
门是锁的,说明房内无人。房门页上那山画的那幅“再见吧,哥儿们!”的粉笔画还是清新如故,可岁月却已经转换了一轮多。仓房里如同那画上所告知的那样,致和悌都没在仓房里,仓房里空无一人,他们俩都被生产队安排出去做事去了,都暂时地都再见了仓房,看来这仓房里只会是我一个人了。
在固定的位置找到钥匙后打开门,门内一股霉气,我擦燃火柴在桌上找到煤油灯,并将油灯点燃,环看了一下屋子内,从四周的蛛网可以看出,这房真有好久没住人了,还可能是上一年的十一月我回来住过几天后就再没住过人了。
尽管过去在这房里我也独自一人的住过,可这天夜里是刚从头一夜的集体宿舍里突然住进来的,这中间的差别太大,一时心理上还接受不了,所以心也难以平静下来睡觉。
反正是坐了一天的敞棚货车,身上衣服己不干净,而我又不是一个讲究卫生的人,我没有管那桌椅上有多厚的灰尘,连行李也没有打开,就一屁股坐在了桌子前,吸起了烟来。
偏西的月光虽然己不能从小窗照进房内,可窗外那山坡上的竹林却依然在月光下轻抚下,竹梢沙沙,婆娑起舞。
忽然,窗外影影约约地飘进来一阵低鸣声,有谁在这夜深人静时还在哭泣呢?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认为是听错了,可再细听还是像清析的哭泣声,这应该不会听错。
但这深更半夜的哭泣声并没有引起我的联想,我也没去再意它,而是继续抽着我的烟,想着自己的问题。
首先是吃饭问题。一个人在队上我是不会想自己动手做饭吃的,这饭还是搭在队长家去,尽管是没有饱饭吃,可还是能让我图个聊别,省心。再就是还是要找队长,争取去外面做派工,那样既能吃饱饭又能多赚点工分,一举两得,不像在队上,拿着那七分五一天,在队长家吃还吃不饱。
正想着这些,忽然门外传来脚步声,这晚怎么还有人来找队长?纳闷时又听见有人叫老X,这不是队长的声音吗,他干什么去了,这晚还没有睡?听见队长叫,我应了一声,就听见上楼的脚步声,我赶忙开门,队长己到了门口。
队长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告诉他,我回来一会了。
我问队长怎么这么晚还没有睡,他告诉我,说队上XX家的爹爹死了,他在那里帮忙守夜,并问我去不去。
那个年代的我可是最怕见死人的,总担心那死人会突然爬起来扑向自己。更担心世上真的有鬼,那死人会变鬼来缠着我。这都是小时候在我家小院内听大人们说鬼的故事太多的原故,使我一直以来就怕鬼,怕死人。
记得小学四年级时,我们院内有一家的男人上吊自杀在家里,晚上使我兄弟俩在父母不在家时根本不敢回家睡,就坐在隔壁邻居的爹爹娭毑屋里,硬是要等他们送我们进屋,并等着我们睡着后才得离开,是这样过了半年多才好一点,可吊死人的那一户人家却几年后还不敢去,就是晚上从那家门口过身还有些心虚。
文革开始那年的秋天,我家邻居爹爹死了,待我们就象亲孙子一样的爹爹我都怕,宁愿住在红卫兵组织的办公室里也好几个月不敢睡在家里。
生产队牛栏屋转角的吊脚楼下摆放着一口大棺材,这是我们出生产队最近的路,大白天我一个人经过这里时心里还紧张,就更莫说是晚上,这晚我一个人回队时就是胆寒发竖地走过那里的。
可这一个大男人怕这总不是光彩事,从不敢跟别人说起,胆小怕去,也不能直接了当的回答队长说不敢去吧,我告诉他说我不想去,队长见我没答应去也就独自走了。
队长走后我关上了仓门,可那胆怯的心却敞开了。仓房里仿佛一下子生滋生出许多恐惧的幽灵,弄得我心怀戒备,神形紧张,房内有一点点的响动也会惊出一身冷汗。
后来这一夜真不知是如何渡过的。
白天队长他在死者家里帮忙处理丧葬,我不想去,没工出,一个人在家又无事,就跑到公社集市上去买了一些东西,邮局去聊了一会天,吃了一餐饭后回队,下午又去八队同我一道在麻阳挖过隧洞的XX家坐了一会,到吃过晚饭才回的队。
回队后在队长家坐了一阵,跟他聊起了仍想队长安排在外做工的一些想法,及在队上出工时伙食还是搭在他们家,同他们一道吃。
队长说:眼下正是农忙季节,生产队今年是三亩多田的双季稻,大队公社的派工插田时节都还要回队出工,一时还不好安排我出外做事,要我在队上先做一阵,等插完田再说。
队长还跟我说,说听说我在修三线时表现不错,希望我回队后也好好干,我的事他会考虑的。还说我们三人中数我出身最好,只要我干得好,应该是最先调上去的。
既然队长是这样说了,我也只好按他说的去做,争取能早日招工回长,离开这贫穷落后的山村。
回到生产队后,又回到了过去那种孤苦、贫乏的单调生活中。致与悌这时在外面做事,很少回队,就连插秧时他们也争取留在了工地没有回队,因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正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少,也就没有矛盾发生。
他们偶尔回队来打一转,就跟做客一样,吃上一、二顿饭就走,还是在队长家吃,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不存在做多、做少,更不存在吃多、吃少的问题。
因为第二年整个一年我只在生产队住了十来天,其余时间都在三线铁路上修路,在外修路计满分,所以,第二年我的工分是全生产队最高的,有三千六百多分,生产队的第二年年终决算时,我一个人分的口粮就有六百多斤谷,还有六十多元钱,只是这六十多元钱仅仅只是一个账,兑不了现。但也比上年年终决算时的二百七十多斤谷,十七元多钱,好出了许多。

